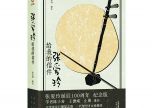拿到稿费转头就去买口红,“爱玲爱玲年”回顾张爱玲“矛盾”的一生
今年九月是张爱玲诞辰一百周年,从年初起有人就戏称2020年是“爱玲爱玲年”,这位沪上传奇女作家的身影又一次来到聚光灯下,尽管她从未远离过。
作者:张玉瑶

对张爱玲的追念如同一场民间庆典,除了铁杆“张迷”,连略知一二的普通读者也都欢喜而纷攘地试图参与进来——譬如对即将上映的由张爱玲小说处女作改编的同名电影《第一炉香》,人们从立项起就持久地关注,并乐于抛出各式各样的“指导意见”,小到葛薇龙的“粉扑子脸”究竟是什么样的脸,大到小说里的“无边的荒凉”是什么样的荒凉,每个人都不惮于自称是张爱玲的模范读者,仿佛在无形的空间中连缀成一个关于张爱玲的交流沙龙。可见她不仅拥趸众多,她的小说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一般读者的基础文本。曾经在经典文学史排位中没有座次的张爱玲,如今几乎成了现代文学作家中读者最多、最广泛的一位,今天的时髦年轻人依然徘徊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滩,依然在寻找那枚“三十年前的月亮”,依然在聆听那万盏灯火夜晚里咿咿呀呀的胡琴,或许是张爱玲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正如张爱玲最经典的两本集子标题,她一生充满“传奇”,充满“流言”。她总是那样矛盾:生于华丽之家,是李鸿章重外孙女、张佩纶孙女,却决然从父亲的家中叛逃;青年声名鹊起,粉丝广布,晚年却孤身潦倒于异国,状况欠佳,死后数日才被发现;受到洋派的教育,以优异成绩考取伦敦大学(后因战事转入香港大学就读),写一手漂亮的英文,却一生倾倒于《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传统文学,爱之弥深钻之弥坚;做一个知识阶层的女性,又无比欣欣于普通小市民世俗生活的细节,还写得那样活色生香的趣味;笔下写尽了婚姻爱情中的心机、算计、博弈、战争,到了现实里的她自己,却“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与胡兰成“今生今世”的恩怨纠葛令人叹息……然而正是这些矛盾和谜团,才让她更加迷人,也更加真实——当大时代潮水落幕、号角声渐隐,是这样一个在菜市场看人家买了什么菜、在枕上听电车响才能睡得着觉、得了第一笔稿费转头就去买口红、乱世里惟愿与爱人岁月静好的女子更与我们亲近,与每一代人的生活亲近。政治战争再久,久不过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英雄再多,多不过时代里的普通人,她是“变”中的“常”。

《传奇》初版于1944年8月由上海“杂志社”印行,封面由张爱玲好友炎樱设计。
“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胡兰成此言有些做作的文艺腔,但张爱玲真正是用自己的人生践行了她的“华丽与苍凉”美学。一朵水中花,开在乱世。1943年下半年,她像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短短几个月内一口气接连发表了《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传世名作,那时她才仅仅是一个23岁的年轻姑娘,却已写尽世间爱与人性的悲剧性本质。“出名要趁早呀”,人们总记得这句,却忘记了她接下来说的,“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乱世里一切抵不过“此刻”,一切浮华后面都藏着“惘惘的威胁”,极目望去,底子里是悲观的。
就像人们无比喜爱张爱玲的语言与修辞,那些想也想不到的象喻满篇摇曳如缀琳琅宝石,然而金句频出之下,掩着的却是人性的恶疾与苍凉底色,机智与装饰衬出的是素朴的众生真实,华袍上爬满了蚤子,啮人的心。就如《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两个聪明人在一句句机锋中过招,却在沦陷的炮火中结成了最平庸的夫妻,但这实在也是战争时代里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境遇;或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白玫瑰是黏饭粒,曾经沧海的红玫瑰终也抵不过变作蚊子血的命运;还有《封锁》中,不稳的时局里,更多普通人不是冲上街头,能做的只是在电车上画画、看报纸、做一场发昏的恋爱梦。这是张爱玲独有的“参差的对照”,但它比壮烈更真实地描摹着时代,有更深长的回味和启示。
今天的张爱玲,当然有了更多的符号意味。她对女性深入骨髓的描写,让她成为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对象;她笔下上海和香港的“双城记”,被作为都市文学的研究文本,还被纳入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的视野;她在传统文学史叙述中地位的变迁,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学术之外,她还是“小资的祖师奶奶”、“文艺青年必备读物”、“影视改编重镇”,更遑论无数八卦谈资……然而无论世事变迁,张爱玲有很多面,却永远只有一个,后人学也学不来。我们一想到张爱玲,始终还是那样穿着旗袍扬眉傲视的模样,清瘦,聪明,嘴边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惟有一代一代的读者前赴后继地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相互致意:哦,你也在这里吗?
(原标题: 百年爱玲:华丽回眸,苍凉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