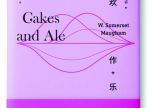如何让小说回到审美艺术的轨道?要注意不为写故事而写故事
卞晨绚写小说,是一个令我意外的发现;待到读完《鲸落》这个中篇,这种意外更加重了一重。她的作品有着与通常所见文学期刊的小说不一样的相貌和气质,例如重视故事到了精雕细琢的地步,其中甚至不乏在远离日常的历史纵深中“创世”的魄力——这些仿佛都不该是她这个代际的作者笔下应该有的东西,如果有,也应该在网络小说中。但显然,我们不能把“有故事”的小说都看作是网络小说,她精致化的文本及其透过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主题取向构不成消遣阅读的商业卖点,不是消费性文本所能够比拟的。
作者:桫椤

卞晨绚
“好看”,就一定是有故事。自有文类分化开始,与诗歌、散文这些抒情性写作不同,小说在语言之上,故事该当是最重要的元素。读起来最顺畅的故事是符合常理的故事,所谓“常理”,无非就是虚构的情节可以在现实中被还原。小说家的困难在于,要在“常理”中不断制造新颖感。至迟从先锋写作开始,经过严肃文学长期的创作实践,到现在小说里的故事都被我们讲坏了。时间被搞乱;空间拆得支离破碎;没有一条明晰的线索;人物常像赛场上的辩手咄咄逼人喋喋不休,叙述者也跳出故事絮絮叨叨。故事被语言的形式遮蔽了,读起来玄之又玄,毫无趣味。
青年作者好好地写故事是难能可贵的,卞晨绚在典雅的叙述重新建立了故事的意义,这种对小说的理解和写作的耐心可圈可点。《鲸落》从“我”的自述起笔,开篇不急于推进情节,而在交代祖母的现状、经历以及辞别祖母的场景上盘桓,并直陈由祖母“把幸福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下场”所导致的命运悲剧引起的自我反思:“从小,我就诅咒着这样的命运,发誓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也绝不让自己过同样的生活。”而这位已经疯掉的祖母,是西班牙女王胡安娜陛下——“我”,就是女王陛下的孙女,皇亲贵胄,但是“我”又是一个漂泊海上、杀人越货的女海盗。身份上的巨大落差造成的空白为传奇故事埋下伏笔,同时也为引诱读者准备了强劲动力。此后作者仍然不急于交代首末,依旧不疾不徐,将回忆缠夹于对海盗船上凶险生活的现场记述中,“图穷匕见”般地揭露出一场巨大的宫廷阴谋,而“我”不过是那场阴谋的牺牲品,一颗在权力和利益面前随意可以被抛弃的棋子。从设疑到解谜,从断环到补环,从留白到填充与渲染,在这个过程中,“我”看透了权力间阴谋的险恶,感觉到了亲情可随时被权欲替换的悲凉,但同时也在爱情中得到救赎。
人物的经历和命运的曲折跌宕造成的传奇性,也得益于叙事节奏上的舒张有致和结构上的疏密有间,而填补行动片段间裂隙的,则是对人物心理、情感的精准把握和细腻描绘。作者不隐晦什么,讲就讲清楚,象征和隐喻并不重要,无论是与“蓝鲸”海雷丁的感情还是被行动上有贵族做派的二副杰拉德的悉心保护,以及在大海中惊恐逃生时的孤注一掷,都被直白表现出来,带给人的冲击力是直接的和强烈的,这不是凭借读者的审美经验再对语言和修辞进行去蔽可以达到的效果。
这种写法在《江南可采莲》中得到进一步发扬。这篇语言和叙述有《红楼梦》韵味的作品,讲述了一个热血的爱情故事——不是所有的热血故事都需要往家国情怀的主题上靠拢,人物的结局回馈浪漫而又朴素的真情也许更重要:爱情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可以超越历史,然后永恒。
故事中“热血+爱情”的模型非但不令我们感觉乏味,反而产生了代入感。当然,小说并不为写故事而写故事,乃是出于塑造人物的需要。故事讲好了,人物活了,小说就摆脱了那种说教式的观念推销,从而回到审美艺术的轨道上来。分析卞晨绚的这两篇作品,我们从中看到她编织故事时的开阔格局:在对经验的抽象、重述与再造中,能够远离现实和当下,在历史纵深处建立叙事空间,从而通过时空距离消解日常生活的琐碎感和庸俗感。前说“象征和隐喻并不重要”,是作者不使用多少意象,但总体而言,故事总是隐喻了现实,这两篇作品有明确的爱情指向,无论人物中间经历了什么,结局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情感故事的走向如果放在生活化的叙述环境中,传奇了就是“狗血”,亲密了就是“傻白甜”,难以做到合常理又有新意。卞晨绚的方法是选择让历史为小说加持崇高感,有效规避了流俗的风险。但世界是复杂的,这种写法需要驳杂的知识作为支撑,而卞晨绚恰恰做到了这一点。《鲸落》中的航海学与地理学知识对情节有着积极影响,《江南可采莲》更不乏大量历史和军事材料,由此可见作者的功底与视野——具体到一部小说不一定非是“百科全书式”的,但每一个好的小说作者都必须是“百科全书学派”的成员。
(原标题:让小说回到审美艺术的轨道)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