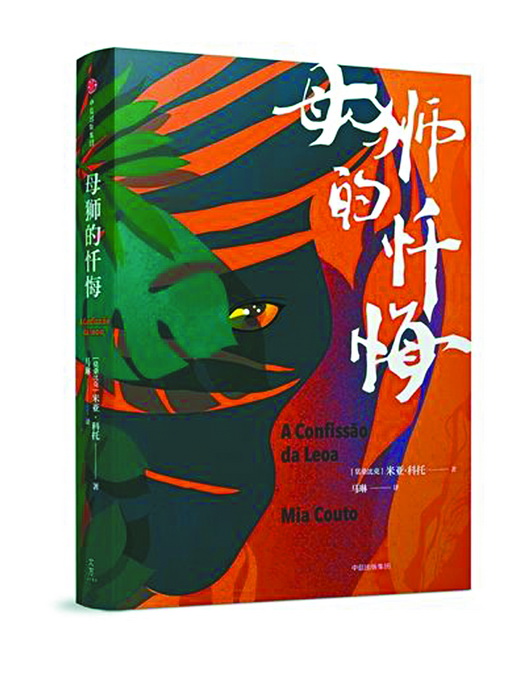狮子为什么袭击莫桑比克女性?还要听这只伤人的母狮“自己讲”
“我来自非洲。也许你们期待我利用这次讲演来诉苦、指责别人或是推卸我身边人的责任。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同时既是牺牲品又是加害人。我想说的是,某种进程造成了非洲的贫困,如今,它也正在以同样的方式阉割我们作为故事创造者的普遍与普世的条件。”
作者:小熊
《母狮的忏悔》 [莫桑比克] 米亚·科托 中信出版集团
以上这段话,引自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2008年在斯德哥尔摩国际作家与翻译大会上的发言,译者是闵雪飞。就在同一年,莫桑比克北部一个叫帕尔玛的沿海村镇发生了狮子袭击人类的事件。作为生物学家的科托当时正在这里考察,他被当地人带领着看到了部分尸体,之后吓得跑回帐篷,在惶惶不安中,科托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作,直至天明。
十年后的今天,当《母狮的忏悔》一书的中文版来到中国时,科托在给中国读者的序言里写到,十年前躲在帐篷中的那一夜,他已经开始了这本书的创作,只是自己后知后觉,久久之后才意识到。
《母狮的忏悔》虽然只有十二万字,但其中涵盖和想要表达的内容之丰富,让这本书显得异常饱满。小说采用双螺旋叙事结构,以两位主人公的第一人称视角交替叙述,带出各色人物。这两位主人公,一男一女,女性是想要逃离村庄、姐姐刚被狮子咬死的马里阿玛,男性是被村长邀请前去库鲁马尼猎杀狮子的猎人阿尔坎如,他称自己是最后的一个猎人,而这亦将是他最后一次打猎。
伤人的母狮是贯穿小说的主线,但米亚·科托想要说的远比这条主线要多得多。从主线引申开的,是一张大网,这里面讨论了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讨论了后殖民时代非洲人的处境,;讨论了外来观光者如何带着猎奇心态走近非洲;,最重要的则是这里的女性所承受的多重剥削与压迫,这里既有来自外部的压迫,也有来自内部的抑制,就像科托在演讲中所言“我们同时既是牺牲品又是加害人”。他希望人们可以更立体地看待今天非洲的现实处境,不是简单化、单线条地把事情仅仅归于某一个原因。
狮子伤人事件的发生,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人类打破了大自然的平衡。曾经,狮子和其他所有动物一样,生活在从未安静过的世界,那里即便是草木生长、花瓣凋零,对动物们来说也是巨大的噪音,他们依赖听觉在野外生存。但是,“假猎人们连幼崽和怀孕的雌性都不放过,不顾及禁猎期,甚至入侵野生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权贵给他们提供枪支等一切物资,让这些杀手活在武器、金钱和权力的三角阵中”。阿尔坎如在阐述自己是最后一个猎人时,说了这样的话。是的,在他眼中,其他依然拿起枪狩猎的都是“假猎人”。
在阿尔坎如看来,狮子伤人的原因显而易见——农民们把小型动物都解决了,那可是大型食肉动物的饲料,饲料没有了,绝望的动物们就来袭击村民。
不论是大型动物还是小型动物,人类都不愿意放过,最终,自己成为了大型动物的口粮。
和猎人阿尔坎如一起来到村庄的还有作家,他代表的是外来猎奇者的视角,他来到村庄,满足自己的窥视需求,同时希望用“新鲜的”素材,完成一部巨著。但讽刺的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城市作家在村庄里举步维艰,他不知道如何面对脚下的土地,就连行走这样的小事,他也需要猎人做他的导师。
一方面是对脚下这片土地的陌生和不适,另一方面,作家也带着外来者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在和猎人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对打猎这件事提出了异议:“我其实持反对意见,希望这不会冒犯到你。”“反对什么?”“猎杀行为,尤其目标还是狮子。”“亲爱的作家,问题是你还没有见过狮子。”“我怎么会没见过?”“你只见过野生动物图册里的狮子,并不知道狮子到底是什么。它们只在自己的领地显露真面目,在那里它就是王。你跟着我到野外丛林,才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狮子。”
在前往村庄的路上,猎人建议作家尽快适应这片土地,习惯做个属于大地的人,作家辩解自己本来就属于这片土地,猎人丢下一句“这点只能由大地来确认。”后转身离开。
对区长来说,猎人和作家都是他维持统治的工具。猎人要帮他把不利于选票的因素清除(即狮子),而作家得帮他将“丰功伟业”报道出去。当他们长途跋涉九小时后终于来到村庄时,人山人海将他们包围,但都是事先安排的村民,其中很多附近村庄的村民,还要在夜色里毫无防备地赶路回家。区长在一旁大叫:“亲爱的作家,你看到了吗?人民爱我们,爱我和我的政党,把这些都写出来,还要照相。”
村民们因为同样脆弱的命运被困居在一起,千百年来存活在世界的边缘。因此,当突然有外来人对其苦难生活感兴趣的时候,他们感到很疑惑。 “你们想知道这里的人是怎么死的?可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是怎么活的。”
比起狮子吃人这条故事主线,非洲女性所受到的多重压迫是科托在书中从头到尾的另一条暗藏的主线,也是他最想要讨论的话题。村庄里的每个女性,都有着她们各自的不幸。
“女人在屋里忙活,没有身体,没有声音,也没有存在感。”;“女人每天一大早起床,便如同睡眼朦胧蒙眬的战士出征。白天,我们作战,生活本身便是故人。每晚当我们从战场归来,无法从任何人任何事物那里得到安慰。母亲一口气说完所有抱怨,仿佛准备了很久。”;”“你说了和平,什么和平?也许对于男人来说是到了和平年代,但咱们女人每天早上一睁眼,依旧要面对始终没有尽头的战争。”
当又有一名女性被狮子袭击,死无全尸地下葬时,区长夫人终于忍不住发出声音——“狮子就在村子附近转,男人却依然命令女人去看守菜园,命令女儿和妻子在天刚亮的时候出去拾柴、担水。我们什么时候能拒绝?等到一个女人都不剩的时候吗?”
她希望在场的女人都能同她一起反抗。但除了她,其他的女人们只是缩着肩膀,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女性无声无息地身披枷锁,艰难前行,马里阿玛的母亲说这里的女人早就在土里了,“你阿爸埋了我。你阿婆、太婆,所有女人都是被活埋的。”但当马里阿玛曾经有机会离开的时候,她却化身为一个阻拦者。“令她痛苦的并不是我会离开,而是没有人会带她走。”马里阿玛在自述中说道。
女人们被压迫,同时也接受被压迫,科托用区长夫人和马里阿玛的视角及口吻,道出自己心里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我们同时既是牺牲品又是加害人。”就像科托的演讲发言里所说的,他拒绝只是简单地诉苦和指责,而是希望同胞们能够完成自身的觉醒。殖民者、父权制都对这里的女性身心进行残害,多少女人在沉默中死去,即便在活着时,也不说话,不思考,不去爱,不去梦想。“如果根本不能幸福,还值得活着吗?”马里阿玛在书的末端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显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拿起笔,用书写来完成一次“对抗”。有人跟她说,“你要当心,孩子。书写是一种危险的荣耀,会让其他人害怕……”于是,在由男人和猎人住在的世界里,文字变成她的第一件武器。
科托用他的笔,记录下非洲女性的不幸,为马里阿玛构建了一个庇护所。而他又何尝不期待着,在现实生活里,有更多的马里阿玛完成自我觉醒,用知识和行动,真正地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