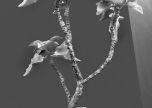北京三里屯:一个让北漂族感觉最熟悉却又最陌生的地方
“去往遥远的北方,论岁数,我过于年轻了,但每个人在他人生的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凭仗,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
作者:木卫二

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对于我,等同于北方。
时间长到让我产生错觉:大概是一到北京,我就住在了三里屯吧。
北漂快十年,我先从黄亭子牡丹园住到了马甸桥东。那地方,是21 世纪初电影人口中的“新马太”(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
混过号称“宇宙中心”的五道口,跟一群朋友喝酒唱K 聚会。他们要么是习惯了熬大夜的网站编辑,要么就是长年失眠、习惯了看片的电影狂。
糊里糊涂地,还游荡过积水潭。那会儿的电影资料馆没那么多精彩节目,我更常去的是牌坊边上的中影集团放映厅。红帷幕搭小舞台,硬板凳配工作桌,分明是老干部开会的场所。
我一再搬家,直到寄居于友人小经厂胡同的住所。这时, 我才真正摊开了北京的地图,发现此前活动的地盘,不过是西北一隅。
春去夏来,胡同迎来了最美好的季节。葡萄架子覆满了绿荫,杨树哗哗作响似落大雨,张妈妈的桌子可以横摆到外头。我在中戏操场上,对着满墙的爬山虎发呆。
这段自我放逐的日子,像在天堂乐园一样无拘无束。我又清楚地知道,一切都是短暂的。如此慵懒散漫的节奏,太不像生活在有三四五六环的北京城。况且,夏天很快会过去, 秋天太短,冬天又长。
有个大晚上,我踩上山哥的单车,去锣鼓巷口的超市买酒。一阵大风从鼓楼方向扑来,槐花飞落,香气袭人。不知电线短路还是产生了幻觉,路灯一阵明暗,火花迸溅。单车上的我也像过了电,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里就是北京啊。
什么电影能代表北京呢?不要说代表,就哪怕是表现这座城市的一个真实截面,在近十年的范围内都不好找。
北京曾是胡金铨的“流沙”,《末代皇帝》的紫禁城。游览中国山川的芥川龙之介却说,紫禁城只有梦魇,只有比黑夜的天空还要庞大的梦魇。
宁瀛的“北京三部曲”,记录了一个粗糙、不修边幅、正在膨胀的北京。置身如今的矩阵迷宫,电影里20 世纪90 年代的北京,已经遥远得叫人怀念。
电影院里当然有北京:国贸桥的延时摄影、三里屯的地标建筑、香港导演想象出来的四合院风情。商业电影为了规避风险,竞相选择将故事背景虚化架空。更有甚者,直接摆上一桌妖怪神魔。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拍什么。
三里屯可能是我最熟悉,却又最陌生的北京地带。
最早光临此地的外国使节、20 世纪活跃的文化圈名流、最新一批的消费主义信徒、脸上挂满稀罕的年轻游客,他们只是经过,从不停留。毕竟,三里屯变化太快。更何况,这里不是地道的老北京。
人们讨论着,为什么隔上一条工体北路,北边的三里屯太古里可以成为年轻人的聚集点——同时也是散装的潮流圣地;南边的 SOHO 商场却空荡荡,全是“洗剪吹”和杂货铺,还有溜冰跳舞的小朋友。附近居民,索性拿它来当羽毛球练习场地。
三里屯这个地名,意为距离北京城墙三里地。从东四十条地铁站,往将来的地铁三号线方向,在地图上丈量一点五公里,不多不少,正好就落在了新东路口上。路口东北角,原来是更大一片的住宅区,名为幸福三村。今天的小区楼,从南 38 号开始倒数,到南 26 号戛然而止,消失的 1 号到 25 号楼,就是三里屯太古里。
三里屯商圈于奥运年开始运营,一开始名为“三里屯Village”,取了“村村屯屯”的本意。很长一段时间,对着出租车司机说出“Village”或是后改的“太古里”,司机都会一脸错愕。总之,还是老老实实说“酒吧街”或者“三里屯”更好。
三里屯不只是一个地名,它还像是一段距离,精准到从这一头往西会撞在看不到的城墙上。不要忘了,那里本来就没有城门。老北京靠东的城门,只有东直门和朝阳门。
城墙不在了,二环里的居民还习惯称自己老北京。这三里开外的范围,已经是新北京的一部分了。新北京与气势惊人、奇形怪状的现代建筑有关。更重要的是,新北京接纳了越来越多的像我这样的外来者。
(原标题:通往三里屯的无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