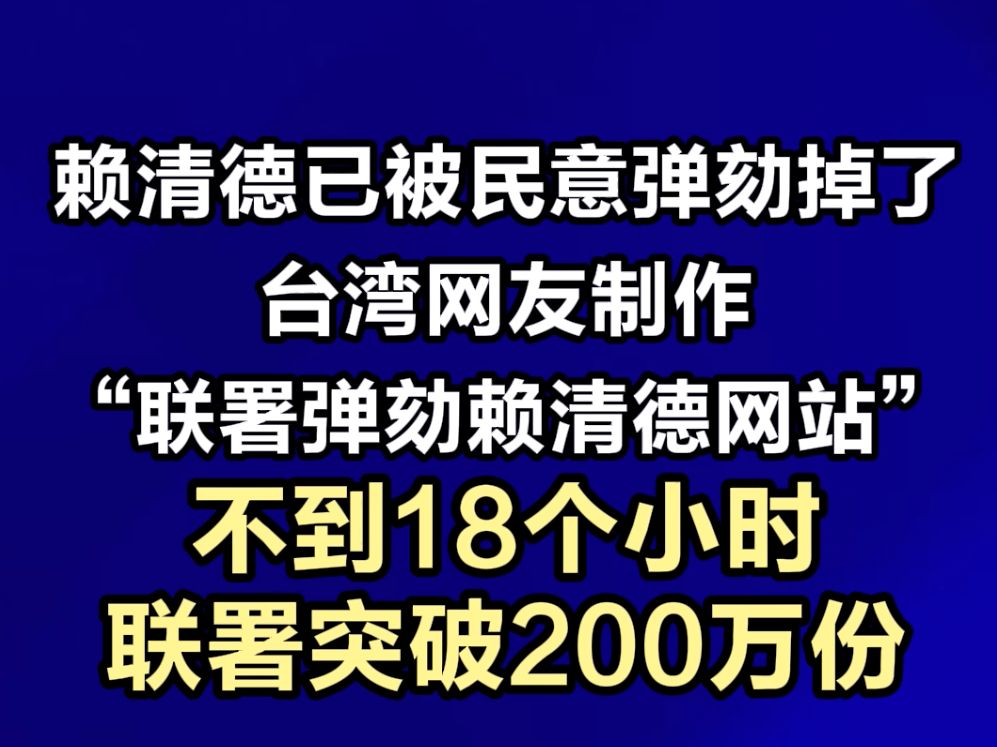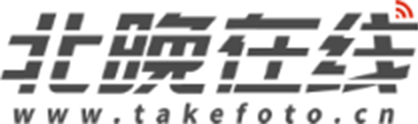壹
看完她2003经典金曲演唱会,我在黑暗中长出一口气说:她多像是从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啊!
爽朗利落,刚烈肯定,你从她唱歌的腔调就能知道,这一定是个说一不二,绝不拖泥带水的人。
她的眼神有时依恋有时决绝,嘴角不时垂下如对影自怜,有时又上扬飞挑,仿佛充满对世间那些莫可奈何的傲慢不屑。而她的声音时如流年似水涓涓细细,时又坚决铿锵,像万马军中绝不低头的疾风劲草。
这是从江湖中走出来的人物,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来自江湖。
她是梅艳芳。
四岁就在香港荔园登台的梅艳芳。
新近上映的同名传记电影《梅艳芳》一开始就还原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荔园的景象,灯火摇曳,其色流金,一个流金岁月就此拉开序幕。这一幕是整个片子我最想重看的场景,它和片尾梅姑在灯火辉煌的红磡体育馆,身披婚纱唱着《夕阳之歌》拾阶而上绝世而去的背影形成了完整的呼应——一个人来过又去过了。
而在我心中,何尝又不是一个年代来过又去过了?
一切从人海中来,又背向人海而去。生死不需要饰演,只有从那个年代跋涉而出的人才知道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
那是个告别的年代,2002年罗文去世,2003年张国荣如破碎虚空般纵身一跃后,梅姑也在年底做完八场演出后转身告退;梅姑之前的十一月,为罗文写过《激光中》、为张国荣写过《春夏秋冬》、为梅姑写过《坏女孩》的林振强过身;稍后的十二月一号,为罗文写过《笑踏河山》、为张国荣写过《侬本多情》、为梅姑写过《胭脂扣》的黎小田也罢笔人间;次年,香江词圣黄霑千山独行。
这些其实并不苍老的人啊,他们像旧时浪头的最后一次浪奔浪流,不必再问君知否,也不必再望着海一片怀念往年,不过是大势所趋下最鲜明的标志性人物,应时随召,纵浪大化,留下这人间满满的心中感叹,似水流年。

罗文、陈百强、梅艳芳、张国荣
贰
在《梅艳芳》之前,我还看了另一部关于她的电影。那是数月前夏至的傍晚,广州下起了暴雨,飞龙在天,龙舟水如约而至。我无意中开始看一部关于梅艳芳的电影——《拾芳》,朝花夕拾芳华绝代。
这是一部梅艳芳的粉丝为了纪念这位百变天后花了八年时间和心血拍摄的纪念电影。电影一开始,是她的歌迷们发现她的一些遗物要被扔弃处理掉,于是想方设法捡拾回来,这是拾芳的由来——她们拾起了另一个梅艳芳。她的灵魂和身体已在2003年12月30日随她而去,但她留下的另一些东西,一些被人以为不再重要的可以当垃圾扔掉的东西,却隐藏着另一个同样真实的梅艳芳。在这个梅艳芳身上,有着绝不亚于那个已经消失的梅艳芳对自己所经历的生命的爱和珍惜。
这些被捡拾回来的东西,多数都是当年梅艳芳的歌迷们送给她的各种小礼物:书信、相片,还有为她写的剧本,它们代表着不同年龄的歌迷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对梅姑的爱。当歌迷们把这些遗物捡拾回来之后,她们根据上面的蛛丝马迹努力去寻找当年把它们送给梅姑的原主人——非常幸运,她们找到了很多,电影,就从这样一种宛如回溯一样的寻找中开始,并且重新发生。故事又重新开始了,在他们各自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记忆里。
看《拾芳》之前我正在看《庄子》,从那些临尸而歌的神仙人物中走出来,突然目睹一个人身后留下的遗物零落的命运,原来遗物本身并没有沾染它们主人的光辉和荣耀,它们被装进黑色垃圾袋后,呈现的是世间贵贱相同的最后命运。而把它们视若珍宝守护一生的女子,她已经没有能力再在这忘情的人间给它们半点保护的力量,所有的遗物都化作了一声唏嘘。
——人生一世,真的惨淡得可以。
身前死后名,对已经远行的人而言可能确实没有太多意义了。但对于还留在这世上,并依然爱着她的粉丝们而言,这些弃若敝屣的旧物,它们却因主人的离去,而有了更惊心的意义。我想,这可能源于离去的主人,曾经用她一生的守护,赋予了这些旧物无与伦比的爱。哪怕仅仅是一张陌生人的相片,她也用她的一生去守护了。寂寞和孤独,有时候可以化作绝大的勇敢和坚毅,那些足够优秀的人物,她们往往都因为自己的孤独和寂寞,成全也成就了自己。

梅艳芳、罗文、张国荣旧照
叁
《拾芳》导演之一是高志森,他拍的好多电影我都很喜欢,比如《南海十三郎》,以及话剧《广州仔黄霑》。这是个情义心很重的导演,喜欢并擅长拍摄过去的时代和人物。情和义,随着老一辈的离开,已经越来越罕见了。幸好,它还在高志森这样的导演身上继续传递着,也在电影里那些歌迷们身上传递着,更在曾经身体力行的梅艳芳身上传递着。香港,这个从传奇中来,也注定将往传奇中去的城市,它生长过梅艳芳这样重情重义的香港的女儿。同样,在无人关注处,也生长着这些重情重义的普通人。
“香港的女儿”这个称谓,据说是叶倩文说的:“每次香港出事或朋友有难,她总是第一个跳出来捍卫,所以大家都爱她,她是香港最宝贝的女儿。”
“跳”这个口语用得真好!活脱脱就像《水浒传》里泼喇喇跳出的一条好汉!
是的!有些人一旦离去,有些品质也就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毋忘情义,长存傲气,日后再相知未晚”,1978年的《陆小凤之武当之战》中,黄霑写下这句词。老一辈关于人间的期待啊,其实都在他们漫不经心写下的词唱出的歌里。
我喜欢那些描写旧年香港的电影,斑驳深邃处,能见到最真实的土地。印象最深的是《叶问:终极一战》,并不飒爽的叶问初到香港,仿佛用他的身影流转,也带着看戏的我们走到了从前。只有省港才有的玻璃窗,它的锁窗结构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大大的扳手,一拉一扳再一扭,好像就可以锁住再大的风雨。拉栅式的防盗门,早已锈迹斑斑吱吱嘎嘎,偶尔从里面探出一张脸,似乎那才是香港这个光鲜的东方之珠被遮掩起来的本来面目。宽敞的骑楼,风雨无阻,骑楼下沿街摆满的大排档,没有《一代宗师》的优雅,优雅是属于个人的修养,但你能清楚地明白,那些红磡体育馆里,那些十大金曲颁奖台上光彩夺目的明星巨星,其实他们都来自这些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巷尾。
1980年,顾嘉辉与黄霑曾为TVB电视连续剧《风云》作了一首同名歌曲,这是一部讲述当年香港经历地产开发时代,城乡两地变迁的剧集。黄霑的词写道:“想不到海山竟多变幻,再也不见旧时面。”那是时代变迁人心变异的交锋口,人们在时代洪流下各寻出路,有的后来万众瞩目,有的终究消殁无闻。在随后的1983年,罗大佑在《一样的月光》中写下:“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随着时代的变迁,就总有一代又一代的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之后的1995年,林振强为梅艳芳填了《歌之女》的词:我记起当天的一个小歌女,她身躯很瘦小;我记起她于不高档那一区,共戏班唱些古老调……
追问的尽头,可能就是个人的记忆吧?这首歌也做了电影《梅艳芳》的片尾曲,《夕阳之歌》后,你才知道,原来要看得夕阳好,并不容易。

梅艳芳2003经典金曲演唱会片尾
肆
我不能肯定我第一次听梅姑的歌是不是那一晚了——我的大学时代正是各种音乐潜流竞相奔涌的时代,摇滚乐、格莱美、港台音乐,纷至沓来目不暇接。但是有一晚,我去学校吉他协会办的一个聚会,长长的阶梯从校门直到行政大楼,其中一个较大的平阶就是舞台,那年代的大学生们秉烛而坐,花样年华在此绽放。吉他还没有插电的认知,一水儿红棉。吉他协会的会长唱完一首什么歌后说,欢迎来自中文系的师兄唱一首歌。这位师兄戴着眼镜穿着软塌塌的西服说:这是首粤语歌,叫《似水流年》。我就真如梦里共醉般,听见了这首歌。
我不记得这位师兄的模样了,甚至直到如今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粤地的学子,但是可真好听啊!
粤语就是有这个本事,腔调都在曲调里,一开腔,时空就变了。
甚至就是因为这首歌,我记住了我的校园。我已经二十六年没有回去了。
很多年过后,我看到了严浩1984年拍摄的电影《似水流年》,当这首歌在片尾荡漾的海面响起时,仿佛真的望见了未来,一片流年,终将似水。
梅姑的歌,快歌是她生活的姿态,慢歌则接近她生命的本然。
快意恩仇的表达往往时过境迁,沉静如渊则更比拟四时不变。
已然小雪。
这人间命定的节气,我所在的广州依然不屈不挠着如同初春的阳光,纵有些许寒意,终究热闹。人间到底是北方的样子还是南方的矜持?我不知道。只是走过路过的时候看见沿途的花会想,花开花谢真的每个四季都会轮回吗?我想,总有些花草,并非年年岁岁都会示现人间的吧?
就像有些人,不经年月,一定不会让你看见。
又是一年了,想起往昔,精彩中有点黯然。
(原标题 一个人来过又去过)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匡笑余
流程编辑 u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