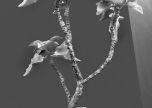个顶个儿:富连成社元字科老先生给票友说戏
九十四岁的高老爷子,耳聪目明,走路稳当,每周在女儿凤茹的陪同下,去周边的京剧票房活动三次。老邻居冯哥也都七十了,开一辆老年代步车,载着老爷子和凤茹前往。冯哥退休前是一名警察,他对京剧未必有多喜爱,但对高老爷子的敬重之心,却非同一般。
作者:天宝

资料图 京剧票友大赛 阎彤摄
我是在护国寺宾馆京剧票房认识高老爷子的,听人介绍他老人家五岁学戏,曾是一位专业的老生演员,唱戏快九十年了,顿觉五十岁开口学唱的我,跟高老爷子之间隔着一座喜玛拉雅山还外带一条雅鲁藏布江。
有高老爷子在,一般都请他唱开场,碰到没打鼓的,他就从随身带的手提袋里掏出个红木梆子当鼓用,边敲边唱。高老爷子一口气唱完“洪三段”,虽说劲头不如从前,但不急不躁,气息通畅,韵味十足。
每每高老子爷见我唱得脸红脖子粗,有劲使不上的样子,就嘿嘿一乐,不用说,我一张嘴他老人家便知问题出在哪了。我心虚胆怯地向他请教,他也不卖关子,说你要学会偷气,不能傻唱,并且现场教我怎样在琴声和唱腔之间用鼻孔吸足气,动静不能大,要不着痕迹,不能让人瞅见了。我试了试,果真管用。可下次唱时,还是忘了怎么偷气,依旧是一口气硬往上顶。
高老爷子笑呵呵送我四个字:缺练欠打。他说要搁在他学戏哪会儿,棍棒早到脑袋上了。高老爷子说起少年学戏的经历,经常是被师傅打得满头包,要是三遍还没记住,没准教棒就杵到嘴里了,能搅出满嘴血,听得我一身冷汗。
跟高老爷子接触多了,大概看出我还算在一点点进步,他已经不满足于我问他答了,常常主动出击,对我的吐字归音,板眼节奏甚至站姿、念白等方面都有指导。念白是我一直还不敢碰的,一是兴趣还不在此,二是感觉真比唱还难。比如《一轮明白照窗前》唱段前有一句叫板“爹娘啊”,就三个字,我从不敢念,总是等过门直接开唱。碰到和高老爷子在一起玩,他就要求我念出来,我不会他就让我跟着他念,这饱含悲怆、荡气回肠的三个字,脑音鼻音都得用上,凤茹姐还录下来发给我,让我回家跟着练习。
高老爷子人和气,会的戏多,知道的梨园掌故也不少。比如有一次我问他《李陵碑:叹杨家大宋扶保》中“七郎儿被潘洪箭射花标”的“花标”二字,老段子里有唱和“芭蕉”、“花椒”的,还有唱“法标”的。高老爷子马上接道,过去是有唱“芭蕉”、“花椒”的,后来据说有人考证过,杨七郎被射杀的地方既没有芭蕉树也没有花椒树, 就改成了“花标”或“法标”,意为杨七郎被五花大绑受刑,背后插了个标牌。过去老先生们教戏都是口传心授,难免有音近字不同的时候。
高老爷子年轻时拜京城名角张春彦为师,被张先生收为关门弟子,不想张先生的女儿看上了年轻英俊的他,又意外地成了张先生的女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高老爷子被分配支边去新疆京剧团,夫妇二人带着七个子女上路,出发的时候小女儿凤茹才刚刚满月。这一去,直到二十五年后退休才返京。现在,高老爷子和小女儿和二儿子同住,其他几个子女仍旧在乌鲁木齐生活。开枝散叶,一大家子如今有一百多口人,早就四世同堂了。
高老爷子叫高元升,是富连成社元字科硕果仅存的几位老先生之一。
(原标题:高老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