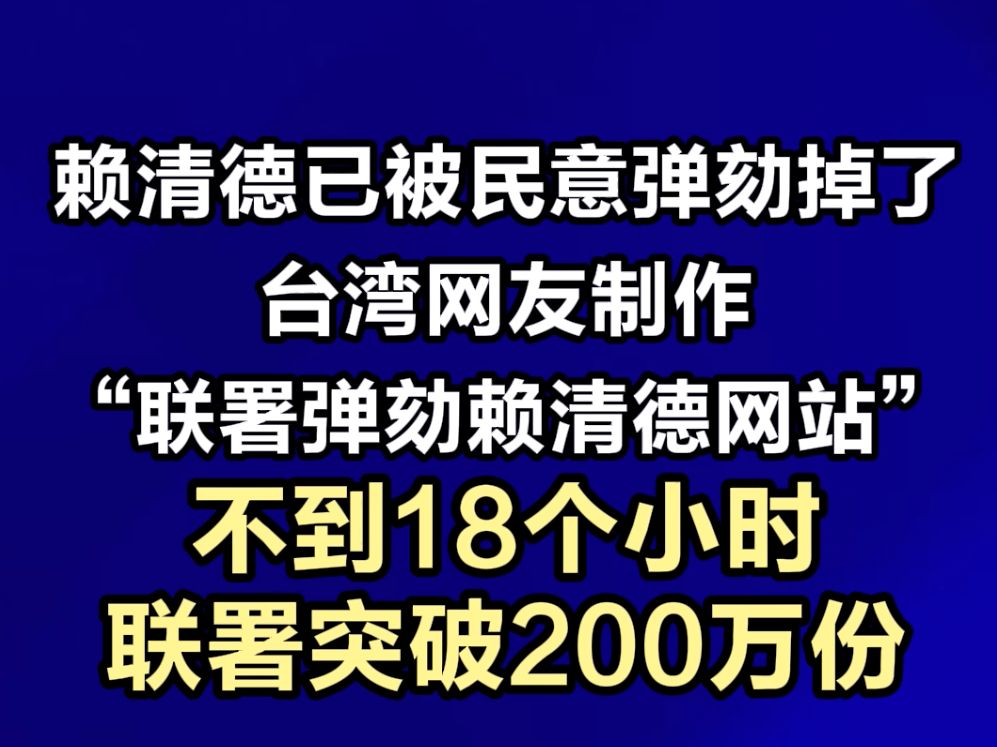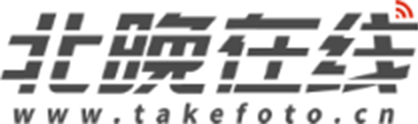北京+
——回望1995世妇会
说起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很多国际友人会提及1995年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简称95世妇会)。时至今日,这仍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空前、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也是中国政府承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性国际会议。
盛会被一些人淡忘。不过,它的遗产却日益丰厚。一方面,日臻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妇女权益撑腰,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让众多贫困女性受益……
另一方面,对世界来说,这次大会成为促进性别平等的里程碑,每到逢五逢十周年纪念时,联合国都会对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以便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平等一代”。在联合国语言中,习惯称这些逢五逢十纪念活动为北京+5、北京+10、北京+15……

95世妇会欢迎仪式

相聚在北京

联合国NGO妇女论坛开幕式

论坛现场

让长城连接我们

在论坛闭幕式后感谢中国

陈慕华一锤定音

为达成共识磋商

和平之声
缘起:为什么不呢?
“在南非,当人们提起‘北京’时,就会想到妇女权利斗争,因为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就以此为议题,产生了《北京宣言》。”今年8月底,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南非召开,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布萨尼·恩格卡维尼在接受专访时,如此描述“北京印象”。
“一提起北京,就想起妇女。”这一说法在国际上很常见,95世妇会时有3万多外宾到来,很多国际友人,通过这次大会形成了对北京的“第一印象”。
龙江文上世纪90年代时,在全国妇女联合会国际部任办公室主任,参与了大会的筹备、会议和后续行动的相关工作。“说起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天一夜也讲不完。”
“1990年,因为西方的制裁和对华歪曲的宣传,外宾人数急剧下降,一个一百余人的团到北京,都会受到很大的关注。”龙江文记得,那年年底,全国妇联接待了联合国妇女地位司司长萨拉米。
接待中,萨拉米提到,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拟于1995年举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她认为,此前第一、二、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非政府组织论坛分别于1975年、1980年、1985年在墨西哥城(拉丁美洲)、哥本哈根(欧洲)和内罗毕(非洲)举行,第四次大会理应在亚洲举办,并询问中国有没有意向。
“一般人都以为世界妇女大会就是妇女代表们在一起开会,其实这是错误的。这个会议是政府间就妇女问题举行的高层国际会议,还有一个非政府组织论坛作为大会的辅助性会议,预计参加人数不下两万人。”
“自1975年起,世妇会每五年举行一次,每次开完会都会拿出一个计划,下一个五年或者十年再开会对这个计划进行检查。95世妇会恰逢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也被看作联合国庆祝活动的重要部分。1995年又是联合国‘国际妇女年’20周年和《内罗毕战略》10周年,所以在这一年办会,备受瞩目,内涵深远。”
当妇联书记处向时任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汇报请示时,对于是否承办95世妇会,陈慕华脱口而出:“为什么不呢?”
陈慕华是我国第二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女性,1988年从副总理任上退下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妇联主席等职,她曾分管过金融和外事、旅游等方面的工作,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事关改革开放大局的好机会。
1991年1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致函联合国秘书长,邀请“有关各方于1995年在北京举行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此前,奥地利政府也正式向联合国发出了邀请。
维也纳还是北京?谁能问鼎1995?中国并无胜算。李肇星当时在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在《说不尽的外交》一书中回忆:
西方媒体对我国的会议设施和承办能力提出怀疑,更声称中国有“人权问题”,造谣说中国不会允许与会者自由活动,不会允许非政府组织和记者自由与会。我们经过一年多的斗争,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1992年3月争取到联合国同意,获得大会举办权,取得了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越是别人觉得我们不行,越要憋着劲把会办好。”同年8月,95世妇会组委会成立,彭珮云任主席,陈慕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李肇星也提前从联合国任上调回,任组委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后来他发现,自己是中国代表团唯一的男性领导成员,这也是他外交生涯中,第一次直接“为妇女事业干点事”。
从纽约回来后,李肇星发现,阻力并不仅仅来自国外。
他刚回国就听到种种议论:不少人说,召开这么大规模的国际会议,邀请几万人来北京,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国际反华势力肯定会趁机制造事端,西方政客会利用这次会议抹黑中国,我们防不胜防。有些同志甚至发出怨言:为什么要办95世妇会?还有的人公开埋怨全国妇联没事找事。
对于大家心里的疙瘩,李肇星能理解。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因为西方反华势力捣乱,以两票之差负于悉尼,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增加了一些人对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疑虑。
钱其琛一直给组委会打气,他坚持认为,举办95世妇会是为了多交朋友、多做工作,让外界多了解中国。“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打破西方制裁,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他还开导组委会工作人员说,“举办世妇会任务光荣,自己不要怕抱怨,而要把别人的抱怨当作鞭策,把工作做得更好。”
为开好95世妇会,李肇星离开纽约前,专门请教了他的好朋友、埃及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加利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全心全意开会的人占少数,一心一意搞破坏的人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既去开会又去主办国旅游;把会开好并不难,把大多数人安排好,防止极少数人破坏,就OK了。”
筹备:这就叫NGO论坛
后来的事实证明,加利的看法是对的。不过在筹备之初,对于与政府会议“打包”在一起的非政府组织(简称NGO)论坛,中方最感棘手。
按照联合国惯例,主办国如果承办政府间国际会议,就要“同时同地同主题”召开非政府组织论坛,以达到政府与民间之间的交流和互相促进。不过,在筹办95世妇会之初,国内连一家被广泛认可的NGO都没有,也没使用过这个名词。
为此,全国妇联第一书记黄启璪专门到内罗毕考察,据了解,1975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一次NGO论坛仅有3000人参加,1980年哥本哈根的第二次论坛有8000多人参加,而1985年在内罗毕举行的论坛有1.3万人参加,由此推算,仅NGO论坛,北京就要接待2万人。
组委会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也派一些干部到国外参会,学习怎么组织一个国际NGO论坛。
谢丽华当时在《中国妇女报》担任编委,并创办了《农家女百事通》杂志。1994年春节期间,她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在曼谷召开的“妇女发展与传媒”NGO论坛。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参加NGO的会,真的是一无所知。”谢丽华说,当时出国需要妇联领导层层审批,批文上一句“外交无小事”,让她颇为紧张。
虽然不是因公出国,没有制装费,“可也不能给中国妇女丢脸啊,于是我就自己花钱买了几件从来不穿的衣服”。到曼谷以后,她才发现这里松散、自由,跟想象中的国际会议一点都不一样。
来自7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穿什么的都有,大背心大裤头的,还有穿拖鞋的,“我带的旗袍、套装反而穿不出来了”。开会时,没有席位就席地而坐,有不同意见的上去抢话筒,吃饭也就四菜一汤,天天一个样。会议间隙,还有代表在摆摊卖东西,说是筹集来回路费。
“真是大开眼界。原来这就叫NGO论坛。”
《农家女百事通》在国内土得掉渣,但在那里一摆,却与论坛关注弱势群体的精神十分契合。倒是那些用外国美女做封面的杂志,常常被人质问:“你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作封面?你们的杂志是给穷人办的还是富人办的?”
回来之后,谢丽华向全国妇联领导建议,“女性杂志封面千万不能用暴露的美女和洋人”,后来,不少媒体为95世妇会出了专刊。还有就是吃饭问题,“一定要用自助餐,一定要节俭,否则人家会质问你们的钱是哪里来的?”这一条建议在怀柔开会时也被采纳了。
交流中的思想碰撞更是精彩。在一个关于家庭暴力的讨论会上,参会的中国媒体人对家暴一词很生疏,还有的人说,那就是夫妻间的小打小闹,中国没有家暴。但一个菲律宾妇女不相信,因为菲律宾华人也有家暴问题。
谢丽华年轻时当过兵,她干脆地说,如果家暴发生在我们身上就离婚。对方竟然吃惊地问,你们女人可以主动提离婚吗?到那时谢丽华才意识到,世界上有些地方,只有男人才能提出离婚。
回来后,她在《农家女百事通》杂志上发起一个讨论:“如何面对丈夫的拳头?”这期杂志讨论得很热烈,甚至男记者们也参与进来。他们发现,农村妇女真要遇上了家庭暴力,即便离婚也会无处可去,因为娘家没有她们能够继承的财产和土地,这就涉及了农村妇女实际的个人权利。
两年后,“打工妹之家”以杂志读者俱乐部的形式,在北京挂牌成立,成为此后一系列“农家女”项目的开端。退休后,谢丽华仍对农家女公益事业不遗余力。
“相比会期只有十几天的95世妇会,之前的筹备带给我的收获更大。”不仅谢丽华有这个体会,很多与妇女相关的事业都可以从筹备中找到缘起:
在北京,中华女子学院和中国妇女活动中心拔地而起;在全国,建立了4470个妇女儿童培训活动基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得以实施,结果表明,8成的妇女“有”或者“有过”工作;
起草多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在1992年颁布实施。会前,又发布了第一个《妇女发展纲要》,提出大幅提升妇女参政比例等任务;
为展示中国女性风采,中央电视台创立《半边天》栏目;“爱乐女”交响乐团在郑小瑛教授的倡议下集结;一大批女性视角的文学作品出版;
……
谢丽华倾向于将95世妇会看作一个平台:它为行动者提供了土壤、肥料和阳光。许多聚焦女性的非政府组织、电视报纸、课程培训应运而生,很多成长于这个时期的人,受到了最初的女性主义启蒙。
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历史性时刻——全国妇联成了中国第一个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龙江文说,通过世妇会,中国认识了非政府组织,理解了这是联合国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实践证明,全国妇联取得NGO谘商地位,能在联合国和其他会议上,更好地为中国发声。
“如今,我国已有103家组织获此地位,这些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宣传中国,维护中国主权,有力地配合国家的整体外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龙江文说。
曲折:怀柔153天攻坚克难
1995年3月29日,距离95世妇会NGO论坛开幕只有153天了。
就在这一天,国务院、全国妇联、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视察了怀柔,正式决定,本次世妇会NGO论坛场地及住宿安排在怀柔。
李肇星回忆:“会前,围绕在哪里接待这么多非政府组织成员,我们颇费心思,最后决定把会址放在京郊风景区怀柔,那里活动场地大,吃、住、开会都很方便。”
在纽约,黄启璪向95世妇会秘书长蒙盖拉传达了中方的提议:经过体育专家的测量,工人体育馆难以承载几万人的活动,要将NGO论坛搬到怀柔。
得知这一地点距论坛开幕式举办地奥体中心至少有50公里时,蒙盖拉的双手颤抖了,与会的各国代表更是“炸开了锅”——反对的声音强烈,就连原来的朋友也开始质疑。蒙盖拉曾说,黄启璪当时带领妇联的朋友是“面带微笑,迎接风暴”。
仅153天,就要把一个预计接待两三万人、期间举行2700次会议的世界级会场搬到怀柔,而怀柔这个名字对世人又是如此陌生,蒙盖拉夫人的不安也是情理之中。
最终,考虑到中方理由充分,也由于南非第一夫人温妮·曼德拉、论坛总召集人坤仁·素帕达拉女士等友人的支持,联合国还是接受了易址提议。
西方舆论可不会放过这个展现傲慢和偏见的好机会。有媒体发布了怀柔的照片,竟然是“茅草屋”;还有媒体说,“怀柔”就是要“以柔克刚”,把非政府组织的与会者赶得远远的,怕他们给中国政府找麻烦。
“我们广泛做工作,争取理解,顶住压力,不为所动。”用李肇星的话说,中国就是中国,不能让几口唾沫给吓住。
外交上寸土不让,现实的困境仍得面对:此前,中国从未承办过这么大型的国际会议。这次,只给153天就要接待2万多外宾,这对于当时人口不到10万的怀柔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计划中的工程量,无异于要重造一座新城:
在153天中,怀柔得拆除破旧建筑物804处;清除垃圾和渣土数百万吨;新建工程40万平方米,所需的大小会议室要新建40余个。交通、通讯、供电、供水、排污,从天上到地下都要翻新扩建。此外,要植树230余万株,铺草坪18万平方米,栽花40万株;粉刷喷涂陈旧建筑物35万平方米……
有人粗算过,这153天的工作量按常规计算,怀柔人需要10年才能完成。
国家紧急拨款,怀柔攻坚克难。会议场馆不够,就在怀柔一中2万平方米的草坪上设置帐篷作为论坛的讨论场所;没有像样的会议中心,就把怀柔电影院翻新作为论坛的主会场。
龙江文和同事们连续数月连轴转,每天要回复“雪花一样多”的国际抗议信,为与会的数万人安排食宿,时常还要参与到怀柔改造工程的讨论,常常是凌晨两三点才离开办公室,早上又回来接着干。
看到国际舆论说要关心弱势的残障群体,组委会就从国外买来了两台可以升降轮椅的汽车。计算到床位不够,就把6个新建小区改成了有热水器的公寓。临近开幕,会议中心外墙仍是水泥墙面,来不及刷漆,只能悬挂印有标语的喷绘布。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奇迹会出现吗?
7月14日,蒙盖拉夫人莅临怀柔,整整巡察了一天。看环境,山环水绕,翠绿掩城;看道路,宽阔通畅,环岛座座;看绿化,树密花繁,美如花园;看工程,栋栋新楼,初具规模。巡视完一个又一个宾馆时,她幽默地说:“这里的房子我全要了,我要把大会秘书处搬到这儿来办公。”
随着五大洲姐妹的陆续到来,这个北京郊区的小县城成了五彩缤纷的女儿国,世界瞩目的中心。
“当时有谣言说,有人要组织上千人的裸体游行,让中国政府难堪。大会筹备处提前准备了4000条毛毯,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裸体游行。”李肇星撰文说,后来并没有这种事。“但有一天,一名日本留学生在前门喝醉,要脱衣服凉快凉快。有位警察警惕性太高,马上用毛毯把他裹上,卷起来送走。这是会议期间使用的唯一一条毛毯,剩下的3999条没能派上用场。”
2.6万名境外参会者,3千多名外国记者,以挑剔的眼光审视着怀柔,但怀柔百姓的热情周到感染了他们,慕田峪长城的壮美征服了他们,哪怕是几场接连而至的秋雨,都没有影响到参与论坛的好兴致。
镜头前,来自肯尼亚的塔瑞莎说,来北京之前曾经听到有关中国会议准备工作的负面报道,现在看到了实际的情况,感到意想不到的周到和有序。在论坛后期,为了驳斥那些不实报道,姐妹们还自发召开发布会。
怀柔创造了奇迹,世界承认了怀柔。从95世妇会到APEC会议,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会都”。
论坛:NGO在北京
作为95世妇会的辅助性会议,世界NGO妇女论坛于8月30日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
“开幕式十分震撼,当从非洲传来的和平火炬进入会场时,当郑小瑛指挥爱乐女乐团奏响贝多芬的《欢乐颂》时,当万千信鸽放飞时,人们手拉手站起来歌唱、欢呼,那排山倒海的气场,是内敛的中国人很少见到的。”火炬传递到黄启璪手中时,龙江文发现,这个工作中柔中带刚的女强人,瞬间泪流满面。
开幕式后,论坛移师怀柔。
参加论坛的有来自近200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3.1万名参会者,其中境外与会者2.6万人。他们自掏腰包、不远万里而来,只为表达自己的主张,日本女性学先驱上野千鹤子也是其中一员。虽然当年的住宿条件很一般,但自费参会,只要房费便宜,就能喜出望外。
中国与会者5000人,有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妇女代表,也有各个行业的妇女精英,另有数千名北京大中学生志愿者,为与会者提供翻译、引路等服务。
论坛共举行了约5000场各类活动,有全体会议、专题研讨会,有培训讲习班、展览会,也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
每天早晨,肤色不同、服饰各异、讲着各种语言的各国代表,成群结队从怀柔32家饭店和分布在6个小区的60多栋公寓中走出,奔赴会场区内的国际会议中心和规模不等的86个帐篷、75个会议室,参加300多场专题研讨会。
在这10天的3900个专题研讨中,由全国妇联统筹的有63个。为了广开言路,一些“草根”组织走到了前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简称妇女所,后更名为红枫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说起妇女所的成立,今年94岁的王行娟总会想起1988年那次“炸酱面会议”。
1988年,王行娟从北京出版社离休,完全可以继续做畅销书作家,但一封妇女来信让她没法安心过日子:一位下岗妇女,因为家庭地位急剧下降而痛不欲生,写信求助“为什么改革开放了,妇女就要回家了?”
王行娟没有琢磨出答案,便请来一群闺蜜,在家里吃着炸酱面讨论,谢丽华、胡舒立、刘伯红等关心妇女问题的学者、记者,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一年,中国最早的民间妇女组织之一——妇女所成立,经费是几个人凑的,王行娟拿出了自己写的畅销书《贺子珍的路》的稿费。
1992年,妇女所开设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此后相继开通妇女专家热线、老年热线、妇女法律语音热线、反对家庭暴力热线等。听说世妇会要在中国举办,她们立即向全国妇联、联合国申请参加会议,并提出承办一场专题研讨。
会前,联合国批准了中国第一批有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这份名单上共有6个组织,第一个是全国妇联,第二个是计生委,其他3个组织是: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南开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和郑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妇女所列在第5位。
给王行娟传递这个好消息的,是时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的刘伯红。她在传真文件的下面,欣喜地写了一句英文成语——“Seeing Is Believing”(眼见为实)。不久,王行娟又收到了全国妇联的回函,批准他们举办专题研讨会。
研讨的主题怎么设置?王行娟认为,需要社会救助的必然是弱势的妇女人群,卖淫的妇女,遭受到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妇女,都是需要社会救助的人群。
但不同的声音此起彼伏:“为什么要谈家庭暴力呢?我们中国妇女的地位很高,为什么要专挑这些问题来说事儿呢?”
好在形势不久就发生了变化,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纲要的第十一条第一次提到“依法保护妇女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坚决制止家庭暴力”。这是中国政府在正式发布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到家庭暴力。
这么一来,禁区打破,组委会也发话了,家暴问题可以在论坛中谈及,我们不仅要谈,而且要组织专门的论坛来讨论家暴。
经过一年的筹备,由妇女所主办的“妇女群体与社会救助”论坛于9月3日上午举办。场地其实就是怀柔一中的一个教室,教室有50个座位,但那天来了100多人,不仅会议室的后面、过道上和门外站满了人,就连前面的演讲区也站满了人。王行娟操着64岁开始自学的英语主持了会议,发言稿上满是英文发音的中文标识。
中方发言的议题包括:中国妇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妇女热线的社会救助功能;家庭暴力问题;单身母亲的扶助;性骚扰对职业妇女的影响。这些如今只道是平常的话题,在当时却都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从否定到肯定的纠结。
像王行娟一样,参会者们没有纠缠于枝节问题,或是简单地喊喊口号,而是充分地发表着各自的观点。比如,当北欧妇女义愤填膺地控诉黄段子和性骚扰时,非洲代表就会打断她们,请她们不要避重就轻,更应该关注到非洲女童仍被施行割礼的陋习。这种见解的多样性,无疑是世界妇女事业的一大进步。
论坛上,严肃的讨论并不是表达观点的唯一形式。在会场区漫游,人们可以看到与会者在认真表演哑剧、小品、诗朗诵、舞蹈、歌咏等文艺节目。爱搞游行也是非政府组织论坛的一大特点,组委会对此早有预案,先划好一块区域,专供妇女们游行用。
有中东、波黑和日本妇女的反战游行,打出“女人不要战争”的标语;有第三世界妇女对大国霸权主义和经济掠夺表示抗议,甚至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有韩国妇女代表的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战”期间强迫韩国妇女当“慰安妇”道歉。
新华社在报道中提到这些活动,形容“妇女们用种种富于戏剧性的方式申明自己的主张”。一位外国代表这样概括论坛上的景象:“在论坛的每个地方,每一分钟都有研讨和交流,每一分钟都有欢歌和笑语……这就是真正的论坛。”
9月8日,论坛闭幕式——“NGO在北京”——雨中落幕,论坛总召集人素帕达拉对冒雨赴会的万余代表说,“在怀柔的10天让我们进行一次空前的交流,在加强原有联系的同时,我们建立了新的关系,在加深旧日友谊的同时,我们结交了新的朋友。”
宣布大会胜利闭幕时,许多外国代表突然展开了一直攥在手中的横幅,横幅上用中文写着“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场面非常感人”,龙江文说,安保人员本来一直对外宾手中的横幅惴惴不安,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盛会:寰球共议“半边天”
9月4日,中国政府作为东道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这也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性会议——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开幕式。
1995年,是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联合国“国际妇女年”20周年。因此,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出席大会的有:冰岛、秘鲁、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挪威的总统、总理或首相,还有27个国家的元首夫人,约130个国家部长级以上的高级政府代表团等,共189个国家和地区的1.53万人。
5260名有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列席了大会。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的3945名记者采访了大会,其中境外记者有3104人。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本打算参加会议,但之前访问非洲染上疟疾,不得不去巴黎治病,为此专门给李肇星打电话表示歉意,并称赞中国所做的出色准备。
在欢迎仪式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直接使用了“妇女是人类社会的‘半边天’”这一表述,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庄严宣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标志着男女平等由此从观念意识变为国家意志,“半边天”因而也具有了性别权利平等的内涵。
从此,颇具中国特色的“半边天”被推上国际舞台。第一次世妇会秘书长赫尔维·希皮拉在会上做了“认识到妇女的半边天作用不亚于人类发现新大陆”的主题演讲。她在演讲中提出:“15世纪哥伦布远航获得成功,人类发现了地球的另一半;5个世纪过去了,人类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半——妇女!”这个世界版的“Women hold up half of the sky”引发了全场的欢呼雷动。
李肇星反思说,有些中文说法译成外文让人难以理解,如晚婚晚育、计划生育等,不作解释外国朋友看不明白,而当一些外国朋友弄明白“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思后,会情不自禁对用“半边天”这么优美生动的话来形容妇女的作用表示赞赏。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引用了“妇女能顶半边天”,估计是参加95世妇会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告诉他的。
希拉里在自传《亲历历史》中说,当飞机横跨太平洋上空时,她的演讲稿已经修改了五六遍,在最终确定草案前,她要求负责审定的外交专家,包括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尽可能给她空间“挑战妇女权利的极限”。
“这次演讲关系重大——对美国,对这次大会,对全球妇女,对我,都是如此”,希拉里是律师出身,曾研究妇女儿童问题25年,这回更是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要一鸣惊人。演讲那天,她特地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件“芭比粉”的外套,没想到却和旁边的联合国秘书长夫人莱娅·加利撞了衫。
“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希拉里的这一说法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中国不新鲜,在世界上,却仍是惊世骇俗的。她的这一说法写入了《北京宣言》,这是她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也是她回忆录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论坛发言之外,各国政府对《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进行着反复、艰苦的磋商,有438个分歧点亟待消除。各方代表观点各异,主张针锋相对,有时还会跺脚、拍桌子以示意见不同。作为大会主席,陈慕华所担负的重任可想而知。
对会议和文件起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陈慕华提出“友好协商、求同存异”的原则,既要尊重各国文化、历史、宗教信仰、发展水平的不同,又要凝聚各方对妇女参与、性别平等的共识。
在她的高超领导和巧妙斡旋下,会议整体气氛较为平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都得到较为充分和全面的反映。9月15日凌晨4时30分,各方终于达成了共识。当然,也有实在无法消除的分歧,只能暂且删除。
会议最终按预期时间圆满结束,这创下另一项“世界纪录”:按时完成了大会的既定日程。前三次世妇会都曾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延长大会的时间。
小槌轻轻击下,《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顺利达成,这是联合国历史上出乎意料又令人满意的成果。
这次大会也被称为“承诺的大会”,这两个重要文件作为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庄严承诺,确定了提高妇女地位的12个战略目标,并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做了机制安排。正如蒙盖拉所说:“这是一次革命,它将给妇女运动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
遗产:不曾远去的盛会
“95世妇会不仅是中国和全球男女平等事业的里程碑,而且是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国际规则和融入世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龙江文在接待工作中对此感受颇深。
她说,1990年代,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了很多不实、歪曲报道。95世妇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万多外宾参会,通过提问和交流,消除了许多对我国的误解。
当外国人还以为中国妇女是三寸金莲时,我们的代表当场举起天足,以正视听;当“藏独”胡说八道时,藏族妇女代表理直气壮地怼回去:“你们到过西藏吗?亲眼见过吗?”
为了增进相互理解,有3000余名外宾在北京参观了农村、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机构。许多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表示赞叹,他们发现,在中国目睹的情况和西方媒体的宣传大不一样,于是又自发回国召开记者会,说出真相。
最有效的宣传是事实。有位欧洲国家的女代表曾激烈抨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她想利用会议间歇去天津市看看,大会秘书处让一位女志愿者陪她从北京老火车站出发。她们在北京站的人海中挤了半天才上车,车还没到天津,这位女贵宾就感叹:真想不到,看来中国搞计划生育不无道理。
会后,还有近5000名外宾到中国各地旅游,在“人民外交”中推动着变革。
1995年4月,马云刚在杭州办起“中国黄页”。没有客户,就把女同学当大堂经理的望湖宾馆发到了因特网上,这很可能是中国最早上网的宾馆。
恰逢95世妇会,一些代表到杭州游玩,点名入住望湖宾馆。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宾馆时,她们回答说,因为这是因特网上所能搜到的唯一的一家中国宾馆。小小的成功,坚定了马云向互联网进军的信念。
95世妇会时,郭建梅被派去采访,“看见她们互相拥抱、激情澎湃、神采奕奕。在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和伙伴,那是精神的东西”。三个月后,她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职务,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
陕西省妇联的高小贤为95世妇会策划制作了一个极富地方特色的“大绣帐”——用十几种不同的布拼成了一只红凤凰。世妇会结束后,“大绣帐”拍出了35万元高价,她以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发起成立了供失学女孩读书的“红凤工程”。
李少红参会时,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中国有多少女导演?“那时候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中国这不是什么问题,光北京电影制片厂就有20多个女导演。”会后,李少红开始思考如何做一个“用女性视角拍戏的导演”。
前欧盟外事委员瓦德纳,95世妇会首次来到中国,在其后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已记不清到访中国多少次。良好的第一印象,有利于她与中国保持良好的沟通,更好地理解中国。
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基塔尼在大会开幕式上所言:“这次大会是联合国妇女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一系列全球会议的高潮,奠定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新时代。”
无论回望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这场盛会都未曾远去。
每当逢五逢十周年纪念时,联合国都会从国家、区域、国际三个层面对95世妇会的决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以促进各项战略目标落到实处。在联合国的语言中,习惯称这些逢五逢十的纪念活动为北京+5、北京+10、北京+15……
一次次回望,一次次评估,推动着进一步的行动: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废除嫖宿幼女罪,加强了对幼女人身权利的保障;2020年5月通过的《民法典》,其中有关于性骚扰防治、夫妻共有财产、家务劳动补偿等方面的规定。
如今,中国建立了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基本消除义务教育性别差距,全社会就业人员女性占比超过四成,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更是超过一半。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世界妇女大会只召开过四次,为什么至今没有第五次呢?2015年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纳赛尔曾联合提议,但终未获会员国授权。
现任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的刘伯红认为,95世妇会所制定的战略目标总体进展缓慢,部分领域进展失衡,差距依然存在,是未能召开第五次世妇会的重要原因。
联合国把北京+25的主题定为“加速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特别使用了“加速”字眼,强调其迫切性。这表明,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北京日报 | 记者 孙文晔
流程编辑:U016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