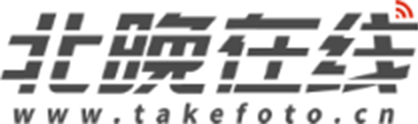《林徽音先生年谱》 曹汛著 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
知名建筑史学家曹汛先生,在《林徽音先生年谱》一书中,将“林徽因”改回她的原名“林徽音”。此名典出《诗经》:“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与上海一男作家“林微音”不相混淆,划清界限,徽音改名徽因。可见,曹汛始终抱有一种情结:追慕与还原,直笔与谨严。作为梁思成先生的弟子,却未与林徽音谋过面,他深以为憾。写作一部关于林徽音的编年史,以年谱纪事,就成为心愿。无论从渊源、师承,还是治学领域看,他都是最理想的书写者。
曹汛先生的文献考证功底,用于考辨林徽音生平事迹、文稿佚作,显得当行应手。编年传统,一向为史家所重。编订文人年谱,对研究传主的交往史、作品史、接受史,极为重要。长久以来,林徽音的形象被定格在“人间的四月天”。一位民国才女,貌美多思,为文人名士所簇拥。徐志摩的追求,又徒增浪漫。“太太的客厅”,一时也成为文化知识界的精神乐园——女主人辩才机敏,引得大批京派文人钦慕。以至于我们痴迷“演绎”才女的“花边”、情感的涟漪,却淡忘了林徽音的“志与业”——建筑学、建筑史、文物保护、工艺设计。
从这一角度看,此书的出版,也是一种归整与纠偏。它是以考据出发,以年谱形式,评述她生平事迹的“别传”。书中,林徽音其人、其事、其作、其功、其友,都得到系统梳理,展示了林徽音从才女到先生的人生全景。我想全书最大特色即简明的丰富,笔笔有来历,字字有出处。如作者发现,林徽音早在1923年就首次发表译作《夜莺与玫瑰》,“一般以为,林徽音是参加新月社后,1931年在徐志摩的影响下开始发表作品,实不确。”
又如,作者推断《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若干封面即是林徽音亲手设计。不下妄断,合理推论,小心求证,既是学人的谨严,也是对传主的崇敬。问题意识,追本溯源,分析考掘,是作者能在细节微言得出新论的关键。如林徽音对文学的兴趣始于何时?“徽音随即结识陈源(西滢),由陈引见和威尔斯结识,辗转介绍,又结识了麦雷和卞因等人。成了卞因的朋友之后,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关于她与徐志摩相识时间,书中也做出辨析,“徽音与徐志摩的初次相遇不会早于是年(1921)春月”“旧说二人于1920年结识,不确。一说二人1921年秋季结识,亦不确”。
理由出自林徽音1931年所写《悼志摩》:“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狄更生先生。”如果参照1921年初,“徐志摩和林长民一起参加伦敦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由林长民介绍,结识了著名作家狄更生”,就可得出准确节点。而文学与建筑的契合,也可能源于另一契因,“在伦敦读书期间,据说女房东(一说房东女儿)是建筑师,受了她的影响,徽音决心将来学建筑。”这种近于环境发生学的分析,显得颇有意义。
大量生活照片、创作手稿、设计图纸等资料,配于年谱之中;各时期代表诗作、文章以插页形式,穿插其间,又形成文本、人物与事件的参差照应。这让我想起张爱玲《对照记》的图文纪事法。它正如乐章与戏剧分幕,见证林徽音各阶段的人生侧重。在作者笔下,林徽音的“两担云彩”——建筑和文学,相互滋养,交织辉映。我们似乎总能发现人生的两分与统一:一半是诗情,一半是理性;一半是明媚的女子,一半是清癯的先生;一边是身心的忧病,一边是精神的丰沛。
动荡战乱,家国之痛,塑造了林徽音的精神肖像。乱世中遗世独立的女性,从同窗到妻子,从同道到助手,她不止站在梁思成身后,更与他携手台前,共进退,度时艰。从童年经历、原生家庭看,林徽音的庶出身份使她从小就有坚忍女子的骨力志气。这是走出脂粉的奇女子,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徽音不得已进美术系,选修建筑系的课程”。
她久受肺病折磨,却走遍大江南北,坚持勘察、测绘等野外作业,“徽音出身名门,又是千金闺秀,还是多病羸弱之身,却能和男人工匠一样登高履险,爬梁上房,她的要强和毅力惊人,今世仅有。”日渐消瘦终不悔,屡遭困厄志愈坚。曹汛先生于书后所附2万多字林徽音小传,正是对年谱的一种“情感内化”。与人格魅力、精神力量相比,风花雪月的浪漫逸事,不足为道。
林徽音的才性,源于锋芒、韧性,同时又不失温暖。她曾像知心姐姐一样,倾听沈从文的情感苦闷;又慨然助人,鼓励后进,“对卞之琳、萧乾和李健吾,都是谊兼师友,亲如姊弟”。《林徽音先生年谱》一书成功将林徽音从文艺渲染、文青崇拜和过度消费之中,解脱出来。它呈现林徽音一生的爱与信仰、志愿与践行。这种感染力,正是那未竟的事业与未尽的才华。
(原标题:那未竟的事业与未尽的才华——考辨林徽音的人生全景)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俞耕耘
流程编辑:TF065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