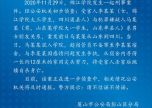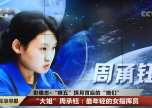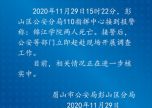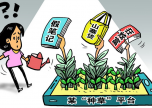独闯“麻风村”34年:“他们会不会瞎眼、流脓、断肢、跪着走路?”
“我听我爷爷讲的,以前我们这个村是麻风村,没有人敢来当老师,农老师就来教我们,农老师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孩子口中的农老师,叫农加贵,是落松地小学的一个普通教师,在他去之前,那个地方没有学校。
“从1986年办学一直到现在,老师都是我一个,现在我们学校只有四年级一个班了,七个孩子。”农加贵说。
这三十四年里,他送走的小学毕业生有一百一十个。
现在这些孩子走出了大山,融入了社会,有当老师的,有当警察的,还有当医生的。
“第一眼看到机体严重畸形的那些家长,我只想掉头就跑。后来也是看着那些孩子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就怎么也迈不开逃跑的步伐停下了。”农加贵回忆。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那顿晚餐”
“碗筷都是新买的,吃吧。”
满满一桌饭菜散发着香味,尤其那碗刚上桌的腊肉,热气腾腾,油光透亮,香味逼人。对于1992年尚属很困难的云南省广南县农村,这是招待贵客的标准。
村长的面容很和蔼,他手上拿着筷子,笑眯眯地看着客人,但就是不动,他要等农加贵和农炳康这两位客人先动筷,客人动过的菜碟,村长一家就不会再动了。
尽管细腻如此,但农加贵心里还是忐忑极了,他不敢动筷,低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喝酒。
“我尽量不吃菜,尽量喝酒,因为之前医生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可以防麻风病。”时隔近30年后,农加贵说起1992年夏天这顿晚餐依旧记忆簇新。
其实,这顿晚餐他无法拒绝。
就在这天下午,他从广南县城第五中学招生办抄回来了“落松地小学”全部10个学生“小升初”的考试成绩,那年参加考试的学生,最高的206分,最低135分,10个孩子全部超过115分的录取线而升入初中。
这是他的第一批学生毕业,而且100%考上了中学。
村长高兴得近乎发狂,这是他们村打1957年建立以来,到1992年整整35年,第一次有学校,第一次有孩子读书毕业并且取得好成绩。
“说不害怕是假话,”回忆当初在村长家吃饭,他说,“我是真害怕,又不敢说出来。”
“不敢吃菜,几乎是空腹喝酒,我喝醉了,是农炳康把我背回了驻地。”
能否留下吃饭,对于这个以麻风病在方圆百里出名的村庄来说,是极端重要的,留下,说明尊重并信任他们;不留,说明来者和外面的人一样,骨子里对他们充满了基于恐惧的抵拒和歧视。
或许,村长那天的挽留,就是一种试探。
我的恐惧心理在逐渐打消。
1986年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有12岁,小的有五六岁。
学生家长中不少人有麻风病,加上感染这种病的潜伏期长达3至5年,所以,农加贵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稀里糊涂地就当上老师了。
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还是按照“医生”所教授的“秘方”,用酒精擦手,也喝了点兑水的酒精,给自己壮胆。
孩子们来了。
随着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农加贵的心跳在加速。
他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他们会不会流脓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来学校?”
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完全正常,没有那些恐怖的情况。
“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爱,我的恐惧心理在逐渐打消。”
再走到教室门口,距离更近了,他伸头看了看坐在里面的孩子,还是没有发现有任何麻风病状,和外面健康孩子一模一样,才按住忐忑的心,走进了教室。
“但心里还是怕,”农加贵说,“说不怕是假话。”
“最主要的是,我待了好几年,没有被传染上麻风病啊。”恐惧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
“农民给我的补助钱币,纱布包着放在瓦罐里消过毒才给我”
一开始,农加贵只有19元民办教师补贴,村民自发从政府给的补助中集资35元作为给农老师的额外补助。
1989年以后,政府给农加贵的教师补贴增加到了每月45元,但村民的集资依旧继续。一直给到1998年8月,农加贵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止。
“农民给我的补助钱币,纱布包着放在瓦罐里蒸煮消过毒才给我”“这35元钱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
“我非常的感动,暗下决心,教出他们的孩子,送出麻风村。”第二年,农加贵主动提出不要再蒸了。
“一些病人跪着用锅铲收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此外,村里还划了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5亩山地种植玉米来给农加贵喂养鸡鸭改善生活,村民们自发帮助他栽种收割。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从1986年以来,已经三迁,即使是今天的学校,也是在原校址上重建的。
“第一次到‘医院’旁边建新校舍,必须推平一个小山包才能盖房子,找了一个开推土机的朋友帮我们平地,样样都说好了,但到要动工的那天,他因为害怕变卦了。没有办法,村长号召全村的成年人用人力来推掉那个小山包。”农加贵说,几次学校校舍新建和迁移,都是麻风村村民举全村之力来参与建设的。
“村民有的赶牛来拉土,有的是3个人一组,两个人用绳子拉擀板,一个人使劲把擀板摁进土里,一趟一趟地硬拉,硬是用了1个星期,把小山包推平,然后村民动手,建起了两间教室。”农加贵回忆。
而在此之前,村民自发集资了8000元用于建校。
现在,落松地小学翻新了好几遍,图书、球场、数字化的媒体设备都进了校园。
“学校小操场的地坪,也是当年村民出力平整后再用三合土打起来的,一些病人跪着用锅铲收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农加贵说。
“只要他们还需要我,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992年5月,也就是因为孩子那年要报考中学,填表涉及“家庭住址”一栏。
“总不能填写‘麻风村’吧?”农加贵找村长商量,得给这个名气很大,却没有一个“学名”的山村起个名字。
“我们村上面有块地种花生,我们把花生叫‘落松’,干脆就叫‘落松地’吧!”村长同意了。
而在此之前长达35年,“落松地”一直叫做“那边那个村”。
“当时谁家小孩不听话老哭,大人就说:‘再哭就送你到那边那个村!’小孩就不敢哭了。”农加贵回忆。
他最难过的是,每学期期末考试,按照规定各学校的老师都要交叉批阅学生的试卷,但没有一个老师愿意到“麻风村”小学来监考。他只能从其他学校要一份试卷,抄在黑板上,再让学生抄下来做。但是每次考试下来学生都很争气,成绩也很优秀。
“1996年那届人数最多,有三个班,我先到高年级把复习的内容教给他们,又到低年级把新课上了。布置好他们的作业。再到高年级这边上新课,上完了又到低年级检查作业,反反复复就这样上了。通过复式教学法,农加贵创造了不可能。
1999年政府把农加贵调到其他学校,下着雨,十多个孩子无论怎么劝都不听,一直把他送到那个学校才回去。
“我感到背后有一批特殊的孩子在等着我,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不久,农加贵又回去了。
落松地村三十多年来所有识字的孩子都是他学生,没有孩子没读过书。
农加贵把大半辈子的青春奉献给了落松地,32年执着坚守,也换得了大山的希望。
30多年来,他一个人教了小学的所有科目,甚至是专业性较强的音乐、美术、体育。他会什么就教什么,即使不会的,他也总想方设法寻找各种资源,比如拷贝一些学生喜欢的歌曲放在电视上让他们学着唱,还会带着学生做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新的数字化、媒体化教学工具出现,他也总是积极地学习。
“我教的七个孩子父母大部分外出打工,好多孩子跟爷爷奶奶住,都是自己在家做饭,不管多晚第二天都会把作业按时交来。”说到现在的学生,农加贵很欣慰。
“长大想当医生,治奶奶的病。”当问及理想,一名学生很认真的说。
“村民们对我这么好,孩子们这么信任我,就让我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一样,只要他们还需要我,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那个地方”,曾经贫困闭塞的落松地村,如今已融入社会,摆脱了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