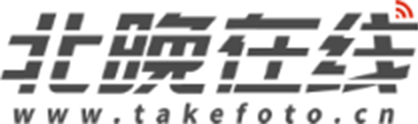如今,金井胡同一号沈家本故居是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教学科研基地,也是许多机关单位进行优秀传统法制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
沈家本先生前后在北京生活了六十年,只有最后的十三年是住在自己购置的金井胡同一号的这所院落。

沈家本故居
宅院建起枕碧楼
其实“金井胡同”的名称,直到民国以后的地图上才出现,因为现在的沈家本故居西侧的金井胡同,原来只是一条从上斜街通往校场五条的狭窄的巷道。留有这条巷道的原因就是这里有一口供给周边邻里用水的水井。这口井正在湖州沈寓大门的东侧。由于冬天井台结冰,取水时常有人滑倒,且有落井的危险,为此沈家本先生命人给井台周边安装上了护栏。由于护栏使用黄铜制成,金光闪闪,人们称之为“金井”,于是这条无名窄巷就有了“金井胡同”的俗称,直到民国初才被正式命名。胡同口的第一宅,也成了“金井胡同一号”。这所宅院,在被沈家本先生买下之前,是在京湖州吴兴(归安)人,为方便乡人来京暂居而购置设立的会馆——吴兴会馆。当时,由于位于广安门内北半截胡同的更加宏大的湖州会馆的兴建,这所总共不到三十间客房的吴兴会馆渐次冷落。由于公选的“会馆提调”沈家本,1893年出任天津知府,他在向同乡会交代了账目,辞去提调之职后,会馆由此彻底停业废弃。
1901年,沈家本在西安行宫,受命任光禄寺卿,为慈禧、光绪一行回京开路,将至北京时,受命任刑部右侍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谕旨:“转刑部右侍郎沈家本为左侍郎”。二月,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三人保荐沈家本、伍廷芳出任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从“从二品”升格为正二品大员,开始了他修订法律的艰苦生涯,为中国法制开启了近代化的道路,为中华法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刚到京时,沈家本暂住湖广会馆。家眷到京后,自然不能久居。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沈家本征得湖州同乡会同意,买下了金井胡同一号已经废置多年的吴兴会馆。留守看管旧吴兴会馆的刁成一家,因为是老熟人,就成了沈宅的管事家人。经过几个月的挑梁、翻顶等土木工程及置办了家具后,时已入秋,沈家人择就吉日良辰迁居。于是这金井胡同一号门前,挂上了“吴兴沈寓”门牌,这个门牌一直挂到1940年院落易主。
沈家本酷爱读书。读书、藏书、编书、印书成了他终生的嗜好。他在天津知府、保定知府任上收集的书籍,陆续托朋友送到了北京。四房儿孙加上自己的住房、书房、厅堂,三进院落已经不够居住。扩建房屋就成了一家人的议题。议来议去竟过了一年,最后还是尊重了一家之主的意见,决定盖一座江南风格的二层小楼,作为书斋,以慰藉老人那怀乡的游子情结,满足老人家建自己书斋的愿望。

修葺一新的枕碧楼
楼址定在前院正房的东耳房并向东推至东围墙,正房与小楼之间留出进入二进院的通道。特地从湖州请来了匠人帮助施工。三爷佑甫(沈家本三子沈承烈的号)总揽其成。直到光绪三十年秋,才算大功初成。虽是木质结构,但两面山墙还是砖砌,房顶的瓦还得按北京的方式装修。南方是直接把瓦排列在檩条上,晚上躺在床上,有时甚至能看到月光从瓦缝中洒下。北方因风大天寒,必须在檩条上铺席,在席上铺泥,在泥上铺瓦,一则防寒,一则防止瓦被风吹落。初建成时很潮湿,不能即时使用,必得晾一晾潮气。再加上置办书橱书柜、书案、座椅等等,一切办得停当也到了年底。上下各四间的二层小楼,上面藏书、写作,下面客厅茶室,舒适、典雅而宁静。
那是1905年之初,光绪三十一年的新年之际,小楼正式启用。还是在董康、章宗祥、徐世昌前来拜年之际,老少四人交谈中,选定了“枕碧楼”斋名。其寓意是小楼枕于碧水之上。一个“碧”字,既代指护城河,又寓指沈家本朝思暮想的故乡湖州旧宅附近的碧浪湖。徐世昌当场题写,董康请人刻制,挂在了枕碧楼正面二层的檐下。
枕碧楼落成后,楼上就成了沈家本藏书与工作的主要场所,楼下成为沈家本待客的会客厅。枕碧楼曾藏书三万余种五万余卷,在京城一时称盛;沈家本先生的大部分著述也都是在这里完成。
枕碧楼的陌生来客
1913年,沈家本去世,沈家本四子沈承煌成了枕碧楼的第二代楼主。
沈承煌是笔者的祖父,因为他老人家去世的那年,笔者刚刚周岁,对他老人家毫无感知。要说他长得什么样儿,那还是祭祖时,从墙上悬挂的影中看到的。笔者所能记录的关于祖父及当初金井胡同一号的情事,都是听祖母赵六如和母亲董曼英的叙述。
沈承煌也曾进过法律学堂,清末和民国时,在大理院做过推事(审判员)。日伪政府成立,沈承煌就隐退回家了。可是他不像他的三哥沈承烈那样杜门谢客,他成天往来于酒肆茶楼,做出放浪形骸、玩世不恭、不问世事之态,以杜章宗祥、董康等旧友之口。
大概就在这时,他染上了痨病(就是肺结核)。那时,肺痨是没有特效药的,整天咳嗽不止,愈演愈烈,以致吐血。有人告诉他,抽大烟既止咳又治病,但因为抽大烟那是伤风败俗的事,自己不能败坏门风。然而,病入膏肓,痛苦至极。夫人赵六如看着他不停地咳嗽、喘息、吐血,真是心急如焚,于是劝慰道:你又不是纨绔世家子弟,不是吃喝嫖赌抽,你是为治病啊,就试试吧,要是不管事就算了,试试也上不了瘾。要是管事,你不是少受罪吗?
沈承煌也真是苦不堪言,自然有病乱投医,而且夫人都如此说了,那就试试吧。一试,果然止咳,也不那么难受了。一开始,家人,特别是其子沈仁坚(字子固,1911-1953,笔者父亲)十分抗拒。但据祖母说,只要一咳喘不止,抽上几口当即止咳,沈仁坚也就无可奈何了。就这样,祖父染上了烟瘾,痨病加烟毒,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沈家本先生过世后,枕碧楼也没有了当初的兴旺,虽然还不至于“门前冷落车马稀”,偶有文人墨客登门拜访,或吃茶、或谈书,但已经不复以往景象了。“七七事变”以后,时不时来做客的客人中,多了一位姓丁的前清举人,此人自称与沈家是世交,可沈承煌并不知其为何方神圣。丁举人每到一次,必定前后院参观,啧啧称赞,时而还隔着窗户往屋里张望,弄得女眷十分不满。但来的都是客,沈承煌也不好说什么。
谁知这贼人竟是惦记上了这所宅院。
丁举人向沈四老爷(沈承煌)提出了购买这个院子的要求。当然,被拒绝了。沈四老爷对他说:“祖传之业,焉能售卖,望勿置我于不孝。”但丁举人并不甘心,仍三番两次提出无理要求。沈仁坚怒不可遏,一次竟将其推之门外,并声言:沈家不欢迎你。
从此,丁举人再未上门,想必怀恨在心。
因得罪日本人忍辱卖房
沈仁坚是沈承煌的独苗,自幼好文字训诂之学,同时又酷爱围棋,曾经在北京小有名气,与当时围棋名人雷浦华、顾水如等是博弈好友。下围棋并不打紧,麻烦的是,沈仁坚自恃棋力,竟赢了日本一名五段棋手,那日本人死不服气,几次三番约至西绒线胡同的一家棋馆对决。沈仁坚不悦,后来就拒绝了这日本人的棋约。
忽然有一天,刁玉 (沈宅管家刁成之子)匆匆进屋对沈四老爷说:巡警刚来过,说是日本人要来搜查,说是有人举报沈家大院里有人私藏烟土,让四姥爷留点神。沈四老爷一听,气得立时咳嗽不止,稍微镇定,问了半天,刁玉也不知所以。又过了一两天,那巡警又来说:“我来知照一声,别在您院子里真搜出烟土,沈四老爷不好办,我们也不好交代。”
这难坏了全家。老爷子一时离不了烟,要是日本人真来搜,即便是找出一两,硬说私藏,也是有口难辩。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危机,全家都不知就里。笔者母亲董曼英后来回忆了此事的经过。
沈承煌问沈仁坚在外头得罪日本人了?沈仁坚说:“就是下棋赢了一个日本人。后来他约我去海丰轩下彩(海丰轩在西绒线胡同,是一个开设棋局的茶馆。下彩,即赌博的彩头)。我不去,他不太高兴罢了。”
沈承煌教训沈仁坚:“你看,跟日本人置什么气,躲还躲不及呢,你就输他一盘,又怎么了?”笔者母亲后来回忆说:“可大家也还是觉得,因为下棋也不至怀恨如此啊。”
全家正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揭开了谜底,他就是觊觎这个院子很久的汉奸——丁举人。丁举人阴阳怪气地对沈承煌说:“听说贵公子得罪了日本人啊,这事可闹大了。”这时沈承煌心里已经明白,一定是此人买房不成,衔仇报复故意挑事。
沈承煌问:“丁老爷有何见教?”
丁举人大言不惭地说:“如若在下相助,此事不难。沈子固(沈仁坚的号)得罪的日本棋手,既然已经知道贵宅地址,也知道四老爷你有食烟雅好,恐怕不会善罢甘休。要是日本人真的上门搜查,沈四老爷恐怕是有口难辩。那日本棋手可不是普通棋手,可是有来头的。”
丁举人按捺不住地说:“贵府不如避而远之,由在下代管此院落,破财免灾,岂不安稳?”从此,三天两头就有日本兵、伪巡警或丁举人到宅中恐吓骚扰。
沈承煌想到了时任伪华北政府政务委员的董康,又不肯舍了气节,去找这位给日本人干事的老朋友帮忙。无奈之下,沈承煌在那张屈辱的所谓卖契上签了字。家人另找房子,经过十几天的准备,打扫好了房子。老宅院这边也收拾好了东西,于是搬家了。搬家这天,丁举人送来了购房银票。祖母赵六如告诉笔者,那银票钱数当时仅够买八袋面粉。
新居在宗帽头条内的城隍庙街。沈承煌说:“沈承煌住进了城隍庙,我命不久矣。”就在当年之秋,抑郁中的沈承煌故去了,享年五十五岁。
不过半年,老人家整天抱在怀里的长孙,年仅四岁的沈厚錧,也因痨病随之而去。
金井胡同一号由吴兴沈寓,变成了汉奸丁举人的产业。
1945年日寇投降,丁举人被民国政府处决,宅院作为敌产被充公。北京和平解放以后,这座宅院与当时北京市政府接收的所有敌产一起,经吴晗副市长批准,作为国有公房租给市民居住。改革开放后,笔者作为沈家本后人、沈家本文化研究者,与法制史研究的学者们多次呼吁将沈家本故居腾退,作为传统法律文化展示场所。
在多方努力下,2017年,这所宅院经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出资,沈家本故居进行修缮。2018年1月18日,沈家本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原标题:沈家本故居的变迁)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沈厚铎
流程编辑:u028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