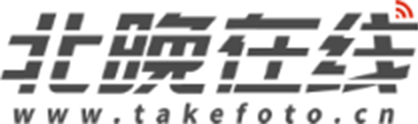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杰作,当时世界的都市之冠,元大都只存在了八十余年,但它让后世的明清北京城有了质的飞跃,中轴线、胡同、大运河等都是元大都留下的宝贵遗产。如今,元大都的2/3面积仍压在北京城下,当考古学家们在此追寻探索时,神秘的元大都只是偶露峥嵘。《北京三千年:从考古发现看北京建城史》从考古的全新视角,带领今人看清一座城的前世今生。本文摘自书中“元大都:《周礼》中的理想都城”一章。
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始于元代。
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原金中都的东北郊,以琼华岛为核心,营建一座新的都城——元大都。马可·波罗在游记里称元大都“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1368年元朝灭亡时的一场大火,让这座曾被描述为黄金铸就的城市沦为焦土。忽必烈的后代逃回蒙古草原后,曾经的皇宫、御苑、圣殿、寺庙、钟鼓楼、观象台……华丽的建筑几乎全部被摧毁或修改,压在了明清北京城下。
元明清时期,虽然留下了一些关于元大都的文献,但古人对司空见惯的事多不记录,关于元大都的记载多是片断的,有些地方反不如马可·波罗这个外国人描述得那样猎奇、全面而生动。
元大都逐渐湮灭,留存的文物太少了,古建筑太少了,史料太少了。即使对北京人来说,它也变成了令人将信将疑的神话。
谁来寻找元大都往日的荣光?一位年轻学者被推到了这一领域的前台。
1956年秋,徐苹芳调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今社科院考古所),从此由书斋走向田野。一有空,他就到清华大学聆听赵正之、莫宗江等教授开设的中国建筑史课,由此与赵正之相识。
1957年5月,赵正之教授作为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负责人,率队踏查元大都遗迹,其中就有20多岁的徐苹芳。那时,赵正之一直试图弄清一个问题: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是否还“活”在现存的北京中?
赵正之注意到,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街巷横平竖直,这种规整的街道布局,究竟是明清时期形成的,还是在更早的元大都时期形成的?经过文献研究、现场踏勘,赵正之认为,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
他还提出,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在北京城市史研究上,这是一次重大突破,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观点。
在北京的南北二环之间,横亘着一系列巨大的古建筑群,从南端的永定门城楼开始,一路向北,依次排列着正阳门、天安门、紫禁城、景山、鼓楼、钟楼等几十座平均年龄500余岁的元明清建筑,总长度达7.8公里,这就是北京的中轴线。
然而,这条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的几何中线并不重合。
明清北京城与北京二环路内的区域基本吻合。从地图上,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从西二环复兴门到天安门的距离,明显大于从东二环建国门到天安门的距离。也就是说,北京的几何轴线在“中轴线”以西,即今天旧鼓楼大街一线。
两条轴线的出现,引发了后世很多争论,其中一个话题便是史学界、考古界争论不休的“元大内”也就是元代的宫城,修在哪条轴线上。
一种观点是,“元大内”以及大都的核心建筑群,建在旧鼓楼大街一线上,也就是北京城的几何轴线上。
清乾隆时期的《日下旧闻考》、近代朱偰的《元大都宫殿图考》、侯仁之的《北平历史地理》等,均支持此观点。其论据来源于《春明梦余录》。该书记载,明永乐十五年,在旧宫殿东边一里的位置,建造了新的宫殿。
赵正之对《春明梦余录》中的这句话作出进一步分析,大意是:很多人都认为“旧宫”指的是“元大内”,但在明永乐十五年修建紫禁城时,元大内早已拆除,所以旧宫不是指大内,而是指朱棣未上位时的“燕王府”。
赵正之还推论说,假设元代的中轴线在旧鼓楼大街沿线,那么由此向南延伸,经过中山公园的五色土,而五色土南侧有一片古树林,其中很多古柏直径都在2米左右,应为金元时期栽种。如果中轴线在此,那么,这些古柏会将中轴上的千步廊阻断,因此元大都中轴线不在这个位置。
赵正之断定“元大都中轴线即明清中轴线,二者相沿未变”。此观点刚提出来,就被戴上了“大都中轴无用论”的帽子。
1960年1月14日,梁思成在工作笔记中记录了学生赵正之的发言,同时记下了学生莫宗江的感叹:“‘没有考虑’许多东西。完全从文献出发。”他还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不平:“大都中轴无用,想不通。”
1962年,赵正之患肺癌,无力写出他的研究成果。在考古大家宿白的建议下,徐苹芳每周到医院一次,记录赵正之的口述,历时两个月。“他说话,声音都哑了。”徐苹芳先生曾对《城记》作者王军回忆,“他也实在没力气了,秋天就故去了”。
谈及自己对北京城的研究,徐苹芳一再强调,他的研究是在赵正之基础上完成的,“只有赵正之先生的文章出来后,我才能讲元大都的事儿”。
1966年,徐苹芳记录整理的赵正之遗著《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本应在《考古学报》上面世,杂志都印出来了,还没来得及装订,便被当废纸处理了。直到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在《科技史文集》第二辑中得以发表。
虽然赵正之的遗著迟迟不能发表,但他提出的问题和引发的争议,一直萦绕在徐苹芳心中。怎么去证明赵先生的观点呢?答案看似简单,文献不能解决的问题就通过考古去寻找证据。但麻烦的是,元大都,用专业术语讲,叫“古今重叠型城市”,并无发掘先例。
此前,对古城遗址的发掘,一般都位于乡村旷野,可大开挖,做大规模的揭露。但元大都的情况太特殊了,它有2/3的面积压在北京城下,不可大开挖。
对古今重叠型城市进行考古,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方法,这对于中国城市考古学而言,意义太重大了。如果找不到适合的方法,就等于将很多有叠压关系的历史名城的考古放弃了,而唐宋以后城市往往都是古今叠压,都有这个问题。
元大都虽然棘手,但让徐苹芳感到幸运的是,它不是完全重叠的。元大都北部约1/3的部分,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20世纪50年代,北二环外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菜地,“一个楼都没有”,这给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场地。
1964年,由中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现北京市文研所)联合组建的“元大都考古队”成立,当年不到30岁、日后成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徐苹芳担任队长。面对二环外的荒郊旷野,他该从哪里入手呢?
当时,北京城内街道的分布,基本是在南北向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地平行排列着胡同。东西向平行的胡同,作为主干大道通往居住区的交通网络,快捷便利;胡同路北的四合院,向阳背风,少有噪声。
徐苹芳意识到,“(以古代的建设能力)要彻底改造原城市中的街道系统是十分困难的,一般都是沿用旧城街道,明清可能也是如此”。
为了证明北京仍保留着元代的城市肌理,他率领的考古队首先在明清北京城的北城外(北二环外),元大都土城墙内的东北部,即元安贞门(今北土城小关)南北大街以东、元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东西大街以北的范围内,用洛阳铲钻探元大都的街道遗迹。
蒋忠义是当年的考古队员,他回忆,幸亏元大都是在旧城(金中都)外平地拔起的新城,通过洛阳铲带出的土层,很容易判断哪里是路,哪里是建筑。“元代土层就在地表以下一米多,如果提上来的土如同苏式月饼皮,是一层层薄薄的小碎层,这种土即路土,说明这里就是元代的胡同。”
“一米一个孔,足足钻探了3年。”这样的钻探工作,从二环外延续到北土城城墙,挖出22条已经埋入地下的胡同,胡同之间的距离为79米。而在北京内城的朝阳门(元齐化门)至东直门(元崇仁门)之间,也从南向北排列着几乎一模一样的22条胡同。
经过全面的考古钻探加上多方考证,考古队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九纵九横的大街构成元大都的主干道,全城应有东西向胡同88条,彻底改变了唐长安城的方块里坊制街道系统,是开放式的街巷。
“元大都模仿宋的汴梁城,采取了新的模式。”蒋忠义等研究者认为,没有坊墙的开放式街巷是大都最重要的特征,两种不同布局形式的城市规划,代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两个阶段。
“一个城市的街道规划布局,犹如一个人的骨骼”,本着这一思想,徐苹芳在弄清街道布局后又对阻断街巷的一个个“框子”,也就是大建筑群的边框,加以整合分析,从而论证复原出了元大都的平面布局。
备受争议的元大都中轴问题,徐苹芳也从道路入手,找到了解密的钥匙。
在《考古》杂志上,他发表了非常可靠的证据:经过钻探,在景山以北发现的一段南北向道路遗迹,宽达28米,即是中轴线上大道的一部分。这说明:“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
单士元在《故宫史话》中提到考古队1964年对故宫进行的钻探:“在文华殿和武英殿取出的土方证明,在两殿的东西平行线上应是元代皇宫的金水河,从景山和地安门桥等地所得资料证明,‘元大内’的中轴线就是明紫禁城的中轴线。”
综合来看,支持“元大内建在旧鼓楼大街一线上”的著作成稿时期较早,依靠的是古籍文献上的“一言半语”。而支持“元大内建在明紫禁城中轴线上”的学者的论证多在考古队成立后,证据是经过科学的勘察、测量、计算得出的。

连街道都追求完美的元大都,为什么没把皇宫建在几何中线上呢?这还要从元大都的营建说起。
1215年,蒙古骑兵攻陷金中都,并将其劫掠一空、付之一炬。1260年,忽必烈意欲迁都燕京,但金中都因种种条件“不符合要求”,最关键的是,千年来北京最重要的水源地——莲花池,水势已越来越弱,成了涓涓细流。
一座全新的都城,必须符合蒙古人“逐水而居”的理念。于是,金中都东北方向的大片水域就成了首选之地。以金朝离宫太宁宫为中心的城市,成了帝国的心脏。这个心脏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已经将近800年,几乎再未改变。

金中都、元大都水系图
元帝国是超级帝国,这样一个国家的首都,建设团队自然非常国际化。主持工程和负责规划的是汉族大臣刘秉忠,另有蒙古人野速不花、女真人高觹(xī)、色目人也黑迭儿等共同参与设计和统筹。
作为元大都的总设计师,刘秉忠的个人经历很不一般,他是大儒,也当过道士,做过和尚。元大都在设计上,将传统汉文化的精髓,诸如《易经》《周礼》、“天地人”等理念融入其中,而“天子居中”则是众多礼法规制中最为基本的,势必成为这位总设计师考虑的首要因素。
为此,刘秉忠首先在大片水域的最东边画了一道南北轴线,宫城以此为轴,又在轴线上建中心台,以此为几何中心,向东西南北各方向进行城建的尺度控制。虽然在此之前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也有类似的方式,但元大都的精密程度,无疑是跨时代的。
有学者发现,当时的城市建设中已经刻意纠正了地磁偏角。地磁偏角是磁罗盘南北极和地理南北极的微小偏角,元代人不但发现而且纠正了。在城市具体的布局中,他们还测设了基线和水准点,其实就是把严密的规划图在地形复杂的场地内放线,进而实现。
虽然从统治者到主要设计人员,汉人都不占多数,但元大都却表现出惊人的中原特征。《周礼·考工记》曾描绘理想首都的面貌,写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大意是,工匠建造首都,九里见方。每边开三座城门,都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宗庙要放在东面,祭祀土地的社稷坛要放在西面。宫殿的朝堂部分要在南面,市场设在北面。
源于周、成书于汉的《周礼》,在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中备受尊崇,在元代之前,中国没有一座都城真的按照《考工记》中的布局要求来建造,但忽必烈下令建造的大都却基本实现了这个几千年来的城市理想布局。
新建的大都,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是金中都的2.5倍,比“方九里”大出很多,但城市的东、南、西三面按照《考工记》的描述,各开了三座城门。北面虽然出于风水考虑,改成了两门,但仍然呈对称布置。大都内道路通达宽阔,绝大多数都符合“经纬”之制。
大都的宫殿、主要衙署集中在城市南部,从城市的正南门至中心台一线,巍峨宏丽,堪称大国气象,对应着《考工记》的“面朝”。皇城的北面,是一个叫“积水潭”的大湖(包括今什刹海和积水潭,但面积更大)。这里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周边码头众多,市场林立。这就是所谓的“后市”。
太庙设置在城市东面的齐化门内,社稷坛安置在西面的平则门内,正好是“左祖右社”。至此,《周礼》对理想都城的描述,几乎都一一实现。
皇帝居住的皇城则承载着草原民族的理想。皇城以太液池为中心,池的两侧布置了四座宫殿和一座御苑,一圈萧墙将它们围起。皇城之内,把宫殿与园林的两大皇家功能区融为一体,把壮阔的自然山水存续在都市中心,这都是草原文明的体现。
作为一个科学规划并严密施工的城市,元大都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闪失”——中心台并没有在城市的几何中心点上。这是为什么呢?
史料记载,当时元大都的施工顺序为:先营建宫城,后筑造皇城及大都的城墙。宫城部分施工即将结束,大都城墙施工开始时,才发现东侧城墙地基松软不宜施工,只好修改方案,进行西移。
此时宫城营建已近尾声,无法跟随修改,况且整座宫城的西侧即是太液池,西移也没什么余地。最终,大都东墙建在了设计位置以西200余米的地方,致使整个大都的几何轴线随之西移了129米。
大都东墙的西移,导致元大内被阴差阳错地置于“非中心”位置上,这应该是刘秉忠始料未及的。在宫城竣工这一年(1274年),刘秉忠无疾而终。不知是不是他的主意,设计者们只得将计就计,寻求破解之法。
这一年,齐政楼(元代鼓楼)建于城市的几何中心点上,在中心台的位置则建起了标志性的中心阁(今鼓楼北)。于是,元大都有了两条轴线:北城,在城市的几何轴线上建钟鼓楼;南城,中心阁向南延伸串联起大都的御苑、大内和丽正门。
元大内不居中,也影响了后世的明清两朝,以紫禁城为主的一系列皇家建筑,皆在这条不居中的轴线之上。明永乐年间,钟楼、鼓楼挪到中心阁旧址的一前一后,中轴线向南延伸至永定门,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中轴线。
元代的中轴遗存,唯一可寻的,就是今天地安门北的万宁桥。它跨在什刹海流入玉河的河口处,曾是元代大运河漕运中的最后一道闸。
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提出,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既考虑漕运方便,又考虑将今天的北海、中海纳入城中,在刘秉忠主导下,在今万宁桥的地方,紧挨什刹海的东岸,确定了一条自北而南的中轴线。可以说,万宁桥就是元大都的设计起点。

元代的中轴线遗存,唯一可寻的,就是今天地安门北的万宁桥。侯仁之考证,万宁桥是元大都的设计起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万宁桥逐渐破败,河道湮废。侯仁之在多个场合讲,这座桥是元大都规划的起点,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城,并力主修缮,恢复河道景观。
2000年,整修中轴线上的基点时,重修万宁桥,意外地在桥下挖出了6只龙身龙爪的镇水石兽,都是元通惠河旧物。那年,侯仁之的90岁生日也是在万宁桥上过的。
在万宁桥东,卧地巨石上有徐苹芳亲题的“通惠河玉河遗址”。玉河,在元代曾是通惠河的一段。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市共有两处河道和两处遗产点入选申报名单。其中,河道就有玉河故道,万宁桥、东不压桥两个遗产点的位置也在玉河故道上。
为了再造玉河,2007年7月22日下午,86岁的谢辰生偕同79岁的徐苹芳,顶着烈日,赶到御河改造工程指挥部,规劝对方不要进行大规模的拆建改造,使对方深受感动,认真向上级做了汇报,改造计划终于得到修改。
数百年来,元大都一直隐藏得很深。但在这几十年间,我们曾有几次机会离这个传奇非常近。
1958年冬,人民大会堂以惊人的速度施工。一天,在大会堂西南角,青年突击队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在意,不料挖出的石头越来越多,随后,一条古老的河道显现在大家面前。
古河道不仅影响了施工,也是安全隐患,侯仁之被点名做水系研究。在汇报工作时,侯仁之顺势提出要编制北京历史地图集,周恩来总理托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带话,对此表示支持,这才有了1986年出版的《北京历史地图集》。
1965年,天安门广场工地发掘的文物在某教委地下室办了个展览,只有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参观,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珍贵的资料都不知去向了。
42年后,国家大剧院施工时,侯仁之的学生岳升阳继续了老师的研究,他发现这一带有金代早期金口河、元初金口河、元末金口新河的故道。
原来,在元大都建设过程中,为了把从西山开采的木材和石料运到工地,同时兼顾漕运补水,忽必烈采纳了水监郭守敬的建议,重开金口河,引永定河水进京,利用了35年。
北京地铁二号线工程,使考古队有机会“大开膛”发掘元大都。当时的考古队分成两组,一组在城东作业,另一组在城西作业。
“没有礼拜天,没有节假日。”徐苹芳骑着自行车两头跑,到了中午,他就在路边找个茶馆,泡壶茶,从包里掏出火烧,就着茶水吃,既能填饱肚子,又能歇歇脚。
1965年秋,西直门内,工人们正在拆除明清北京的北城墙。在已拆成平地的城墙基础下,发现了瓦片、地砖和残破的窗框。考古队员们小心地揭开被明代城墙覆盖了几百年的地层,一片建筑遗址显露出来,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这就是在元大都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之一——后英房遗址。
后英房遗址,是一座元代豪宅的一部分,被压在明代城墙下的恰好是一座前轩后厦的正房和一座如今非常少见的“工字厅”。
这些建筑已体现出后世四合院的很多特征,它们建在高大的台基上,地面全部铺砖,且都采用了“磨砖对缝”的做法。很多房间都做了3面火炕,这些炕不高,只有30厘米左右,与其说是火炕不如说是一圈“地暖”。房屋里还有雕琢精致的木隔扇,连火炕都围有精美的装饰木板。

新影厂升降车拍摄后英房遗址。
这次发现只是一个开始,1965年至1974 年,考古队在北城墙一线挖出十来个元代居住遗址。一座座压在北城墙下的房屋,就像被定格在明城墙中的琥珀,留下了元大都生活的种种细节。
后英房的主人显然非富即贵,他仓皇而逃,地面上散落着222颗由红白玛瑙磨制的围棋子;一块墨迹犹存的砚台摔成了八瓣,砚台上的刻字说,苏东坡本想用这块砚台陪葬,后来被米芾收藏了;发掘出来的日用器物,元青花葵盘几近透明;一件螺钿平脱的漆盘,用五光十色的贝壳镶嵌成一幅“广寒宫图”,制作极为精美;在清理东跨院北房地面砖的时候,发现有贴在砖上的纸张墨迹,纸已经腐朽,而砖上的字依稀看到“娘的宠儿”怎的怎的,应该是元曲词句。

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里,主人仓皇离去,散落在地上的红白玛瑙棋子

广寒宫漆盘
在雍和宫后,有一上层官僚宅邸,房间内出土了玉雕、带饰这类贵重物品。其中一件漆器上面还有“内府公用”的铭文,估计这家的主人与宫廷有关。
挖出来的贫民居所和我家解放前的房子一样。房屋狭窄,地面甚至比门口还要低40厘米。屋内只有一炕、一灶和一个用于舂米的小石臼。
西绦胡同,出了一座类似库房的建筑,墙壁坚厚,东墙尚存3米多高。房内的碗、碟成套瓷器摞放在一起,达半米多高。
寺庙遗址中,石碑、旌杆等均立在城墙之中,碑刻非常完整,记载这是一个叫“福寿兴元观”的全真教道观。
虽然时过境迁,但说起这些细节,考古队的蒋忠义、黄秀纯都如数家珍,足见这些遗址多么生动地定格了元的灭亡。这些房屋,连同屋内的物品,为何会原封不动地被封在城墙里呢?
1368年9月,徐达率领明军攻陷大都齐化门,元朝宣告灭亡。失去首都地位的大都,迅速降格为北平府。从礼制上考虑,徐达入城后必须“缩城”,使城市规模小于当时的国都南京。
入城仅6天,徐达就任命属下大将华云龙,在大都北城中部(今北二环一线)增筑一道东西方向的城墙。这道新城墙仅用20余天就修筑完成,以至于墙基位置的各种东西都来不及清理。
房顶一掀,大柱一拉,无论是房基、砖瓦、石碑,还是旗杆、木料,甚至是垃圾,统统筑入城墙。老百姓虽然都跑出去了,但屋里的东西甚至细软,都没来得及收拾。在考古队员眼里,时间仿佛凝固了。
逃难时,也有老百姓把好东西藏了起来。1970年10月,北京市标准件四厂工人在旧鼓楼大街豁口以东取土烧砖坯时,发现一处瓷器窖藏。窖深不到半米,上面覆盖一个陶盆,内藏10余件青花瓷器及影青瓷器。黄秀纯曾负责抢救这些瓷器,他回忆道:
因为是在明城墙下发现的青花瓷器,至少应该是明洪武年间或之前的文物。我和于杰当时就准备去现场,但受到极“左”思潮影响,一、三、五“抓革命”二、四、六“促生产”,当天刚好是周一,军宣队领导不许我们去。第二天是“促生产” 时间,我和于杰赶过去,发现这10余件原本完整的瓷器已经被工人们“破四旧”,用8磅的大铁锤砸碎了。
元青花别说是完整的,碎瓷片也是非常难得的。于是我们用二、四、六的时间筛了3天,把工人砸碎的瓷片,全部从土里筛选出来。拣回来的残碎瓷片,放在办公室桌子上,大家一片一片地拼对,最终复原出10件青花瓷和6件影青瓷。
那件成为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青花凤首扁壶也在这批瓷片中,由48块碎片粘成,背面几乎残缺了50%。2004年,该壶由上海专家蒋道银重新修复,整个过程历经13个月。
由于地铁工程时间紧迫,明城墙下的这些遗址,发掘后只能拆除。徐苹芳嘱咐考古队员们:“一定要多照相片,我们花几万块钱(发掘),将来能留下的就是照片。所以一定要多照,别心疼胶卷!”为了给后英房遗址留下全景,考古队把毛泽东的摄影师舒世俊都请到了工地,但由于新影厂的升降车高度不够,只能拍出接片。
行进在车水马龙的二环路,谁会想到,路面下还曾有一个包罗万象的元代世界。

(本文摘自《北京三千年:从考古发现看北京建城史》,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著,本文作者孙文晔,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9月第一版,定价:78.00元)
来源:中华读书报
流程编辑:TF019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