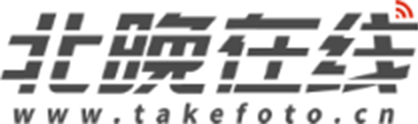一九九三年夏季的一天,黑丰曾在乡下老家的菜园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纸上的漂泊中,我呼唤并期望寻索一种新的地理。我提倡人的不灭,祖先永远活在土地上。文学实则是一种变相的考古学。我们不仅要善于从人使用过的器物中,从历史的遗迹与印痕中,从空间的迷局中给祖先和易失的人类按脉,还要善于从当代人的身上发掘我们的祖先,从而发掘人存在的多样性,进而拓展一种神性的文学新疆界,让比我们更古老的词语重新开口说话。
 《蝴蝶是这个下午的一半》 黑丰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蝴蝶是这个下午的一半》 黑丰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这是具有宗教哲学气质的诗人、后现代作家黑丰,第一次在他的笔下提出了“地理”的概念,凭直觉认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认为“祖先永远活在土地上”,并且推论文学应该是“一种变相的考古学”。文学“地理”的提出,主要经由他的1990年前后几个实验小说的托举和承重,具体形成“地理”这一概念是1993年。
现在看来,仍然是对的。
在黑丰的实验中短篇小说集《蝴蝶是这个下午的一半》中,我们看到了“生命浸淫的汁渍和时间沉淀的遗迹”。比如,在他的先锋代表作《人在芈地》里,主人物“尹”三次遭遇一棵命定的楝树。楝树在作者的表意中,既可是另一情状的“人”,也可是另一种“泥土”。“人”也罢,“泥土”也罢,都是以空间形式显世或在世的。泥土可以理解成一种高举的“地理”,“芈地”通过这棵树升到了空中,“升”是时间页岩的另一种沉降。尹的诞生、尹的童年、尹走下北方那所大学的台阶、尹归故里(芈地),以至尹走入棺木等,都能在这棵树的深处望到。树的“深处”正是这一楝树所处的被日常所遮蔽的特殊区域。这一区域,与你所处的纯物理区间也许是一致的,部分是重叠的;但它未可知的(大片大片的)“页岩”就“叠”在那里,冷冻在那里,你在树下望不到,或很难望到,根本无法切入。
黑丰的写作“考古学”的意义,是空间的,遗迹的(发掘);“人虽不在场,却完全存在于景物当中(塞尚)。”因此,他重视“物像”,重视罗伯·格里耶,重视他的重要代表作《嫉妒》。物体和词语中存在“一种非有机体的生命的力量”,“消亡的是有机物,不是生命。”(德勒兹)
他的小说撇开了传统小说的故事链条,特别强调了地理的因素,强调一种考古学意义的发掘。《第六种昏暗》《人在芈地》《白棺》《黑鸟为什么盘桓》《蛇的弥漫》等多篇实验小说都特别重视地理。譬如1990年写的《黑鸟为什么盘桓》就是一篇特别具有地理性的象征小说。虽然它尚够不上一个短篇的那种特有的精致,但它的价值不在这,而在于叛逆,在于它的延“异”(这正是他所要标示的最可贵的地方)。其实从中国文学传统“延”下的(东西)只能是很小的一部分,重点在“异”(陌生化),重在(血液的)刷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重生。
有一种写作不是承继的、顺从的,而是“反父性的”,它自始至终是一场搏斗——既与他者,又与“孤家”。在此,我们必须用力、用烈火,打倒并销毁“父辈”的永生的金像,只有在残酷的销毁中,我们方得以再生(或重生)。同时,写作又是一种召唤——对那些游荡的、无家可归的虚位“在者”,使那些曾经的“在者”重新临在,复位和安居。
人的这种“反父性”和叛逆,与一个人的个性有关。
所有的写作,最终在于指向并言说一种不可言说,指向并言说天地万物之深奥,指向并无限切近这种感性背后最本质的存在,指向并非沉默论者——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之所谓“对不可言说的必须沉默”。
事实上,地理是象征的。地理中任何一种物像,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们每时每刻都在言说,通过一种未知的语言介入我们的生活。强调小说中的地理性,这是空间颠覆时间,感性颠覆理性。这种颠覆性的地理写作直指一种无法把控的最高理性。
这就是黑丰所认为的地理小说,也是他的小说观。
(原标题:写作,最终指向并言说一种不可言说)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皮相
流程编辑 U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