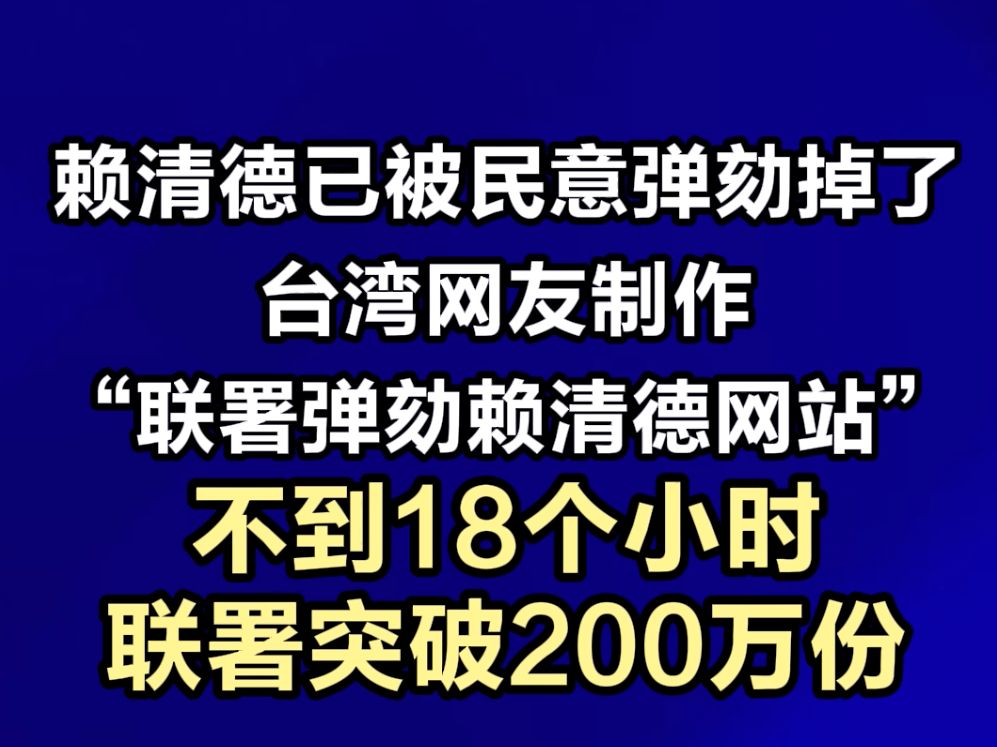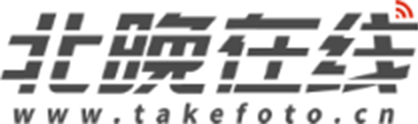厚重的历史,拒绝肤浅的表述。
 《摇篮旁的额吉》 郭雪波 著 作家出版社
《摇篮旁的额吉》 郭雪波 著 作家出版社
三年前的一个冬天,我迎着来自西伯利亚的六七级寒风,走在苍凉的草原上瑟瑟发抖,去寻访一位收养孤儿的老母亲。枯草在摇曳作响,一座白色蒙古包戳立在小湖边,如一只孤独的天鹅,湖水已封冻多半。我走在那片草原上,思考历史,思考土地,思考文学,思考如何描述那些收养孤儿的草原母亲们,内心深处有一种犹如那面湖水向阳处的活水涌动出白色浪沫一般,久久不能平静。那里是科尔沁草原最北部的冻土带,再往北点,就是“苏武牧羊”的苦寒之地,贝加尔湖一带了。
一个写作者,总是遇到各种素材选择,如写什么、如何写。当你面对一个厚重的历史选题时,除了感到幸运,有一种深入体验、探寻历史与文化、可致力深层次厚重些的创作之外,不免还有一种踌躇,毕竟很多人触碰过它了,不好再重复,老调重弹。可当我站在那块冻土地上时,耳边又响起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历史与土地很神圣,面对它的广袤与厚重时,必须要抛弃浮浅与功利,重新进入时更须自重,更须做足功课,去深入,去感悟,真正挖掘出该题材涵盖的更深层次的意义,以及厚重的时代价值。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大地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内蒙古自治区受中央指示,接纳南方孤儿三千余名,在草原上安置抚养成人,书写了一部“摇篮旁的史诗”。乌兰花草原的19岁少女都贵玛,独自抚养二十七名孤儿,一生未嫁,孩子们称呼她“玛乃-额吉”——我们的母亲。蒙古族人民古有“阿伦高娃母亲五箭训子”、成吉思汗母亲诃额伦夫人收养千百个灾难孤儿的历史典故,她们一代一代诠释了伟大、博爱、仁慈、包容、善良等人性美德。我始终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应负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对现实中的真善美故事以及闪烁出历史光辉的重大事件,要有敏锐的嗅觉,去捕捉、去思考、去弘扬。尤其更要细细捕捉那些艰难时期展现出人性光芒的美好东西,那就是人的真,人的善,人的美,人之间的大爱。
这里就涉及一个文学价值取向的严肃问题,你是“审丑”,还是“审美”?中国文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伤痕文学”开山发力以来,这么多年是以批判现实、揭露黑暗、描述人的丑恶及社会弊病为主体的。当然,这种写作并非有错,一些人认为写悲剧更有震撼力。然而,我们恰恰忽略了一样东西的存在,一个与这些黑暗、丑恶相对应而存在的东西,那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人性的真善美,人之间的慈爱和互助。我们的现实生活再无力再无奈,人世间也从未泯灭过人性闪光的真善美,从未遗失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和互助。当下我们的文学目光应该更多关注这些,我们的文学不应失去“审美赏美”的功能,我们更不应忘却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去讴歌光明。
出于以上考虑,五年前我从纯粹的文学角度,选择了对这一历史题材的重新开掘。而且发现,在以往诸多写这一题材的作品中,把重点基本都放在孤儿们如何成长的经历和命运上,恰恰忽略了母亲们含辛茹苦抚养他们的艰难历程,以及其中包含的深刻内涵。写母亲看着容易,实际很难,容易老套,世上太多的写母亲的作品了,如果没有艰世经历,没有与母亲共同的患难经历,没有在母亲温暖羽翼下艰难成长的童年少年,很难写好那些收养孤儿的母亲们的胸怀以及她们的内心世界,更难以塑造她们的形象。
恰好,我自己有一位这样的老母亲,共同经历过那个艰世年代。我母亲是半农半牧地区的一个老妇,因出身不好,一生经历过很多磨难,尤其是在三年大灾中,为抚养我们五个孩子而吃尽苦头,为供我上学赶着毛驴捡杏核、砍柴卖钱,帮人干活,吃野菜中毒差点丢命。可她心灵很善良,为救活死了母猪的小猪崽儿甚至嘴对嘴给它喂米汤,给误吃耗子药的小鸡切开嗉子清洗,还拿舌头去舔,称人舌头上的黏液可消毒,为横胎难产孕妇不嫌脏不怕风险助产等,在村里被称为“善良的额嬷诃”老奶奶。后来,母亲73岁时终于倒下,半瘫痪了身子,大小便失禁。在我们五个子女精心照料下,她活到90岁,在炕上整整瘫了18年。下葬时,全村人为她啼哭送行。我在采访那些收养孤儿的草原母亲时,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仁慈的老母亲。我从她们身上,从这些境遇不同的草原母亲身上,深深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仁慈、温暖、慈祥和永恒的光芒。
于是,五年之后,这部《摇篮旁的额吉》终于完成了。草原上的母亲们,共同谱写了这部隽永的摇篮旁的史诗。
生活是小说源泉,生活中美好的、有光泽的故事,更应该是源泉中的源泉。我一直坚守着这一原则。
(原标题:厚重的历史,拒绝肤浅的表述)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郭雪波
流程编辑 U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