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新作《鸢回头》出版,今天如何读传统?
几年前,作家刀尔登出过一本《不必读书目》,目录里,《论语》《老子》《庄子》《孟子》乃至四大名著等都赫然在列,令人暗暗吃惊。不过翻开看时,原来却是“障眼法”,颇可看作是刀尔登自己的另类读书笔记,尤其着重点出历代的“误读”。最近,他的新作《鸢回头》出版,副标题为“谈谈孔子,谈谈老庄”,可视作是对《不必读书目》中相关内容的扩充与发散。
作者:张玉瑶

这是一部相当个人化的阅读随笔,刀尔登对孔、老、庄的切入点,一如其一贯文风,别致而犀利。面对的虽是古人,是几千年来反复被钦定、注释、重读的所谓传统经典,刀尔登却能另辟蹊径,不泥、不趋、不媚,真正以一个现代人的现代眼光去观照。
《论语》等先秦典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当今人们越来越推崇去阅读甚至让孩子们从小诵读它们,一大原因是认为其作为历代传承的经典,其中富含着人生智慧,格言无数,可以拿来指导生活、进行价值评判,甚至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但刀尔登提醒道,正确借用这些智慧,前提是对人类个性和生活的丰富性有所了解,任何训诫和教条,不管多么睿智,作为简化的模型,都无法覆盖曲折枝蔓的实际生活。更何况,孔子、老子、庄子等人,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里,变革实践不成,方才退而著书立说,“一批不知如何改造自己世界的智者,会知道如何使未来世界更好吗?”在刀尔登看来,孔子固然是“美好社会的向往者”,但不可能也没有责任为后世负责,当代人的问题还需要当代人自己来解决。
两千多年来,孔、老、庄的思想被连篇累牍地阐释,这使我们当代人在今日阅读之时常常疑惑,我们在读的到底是《论语》《老子》《庄子》,还是它们的接受史?从董仲舒到宋明理学,从“尚黄老之学”到竹林玄谈,思想一路被纳入权力结构之中,被改造、利用甚至滥用,离本真面目越来越远。刀尔登在文章中则处处注意厘清脉络,辨明源头活水与沟汊漫流,还原思想原本的生命力。如庄子之学曾颇受儒家学者诟病,认为其祸乱士人之心,刀尔登则一针见血指出,庄子乃是士人在与权力对抗中找到的一条伦理出路,“即使士人对庄子的接受只在皮毛上,庄子之学仍是一件宝贵的武器。有了庄子,人们仍无力还手;没有庄子,则连还嘴的能力也不多了”。
刘瑜曾评价道,刀尔登解读中国历史的文章不仅无毒无害,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在国学热的当下潮流中,此书亦提供了一份冷静的思考,提倡回归一种“伴随历史感的个人阅读”。至于《论语》等典籍,他给出的阅读建议是,不必太辛苦,松开眉头,“不妨读之,最好是用轻松闲适的态度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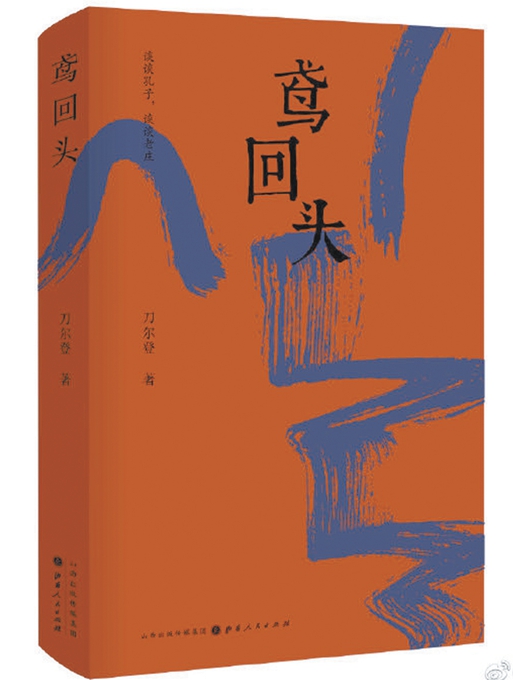
【专访】
我们今天如何读传统?
书乡:您之前在《不必读书目》里写过“不必读”《论语》、《老子》和《庄子》,《鸢回头》又重新对这三本经典进行细读或者说扩充,是如何考虑的?孔老庄三位已经被汗牛充栋论说过多次,这次重读的出发点是什么?
刀尔登:这本书是为杂志写的两年专栏的汇总。当时,除此之外,一时不知写什么,也不知能写什么。这不是一本有学术性的书,汗漫写来,应该算是一种自省,反省心中一些观念和价值的来源。孔老庄确实给说过不知几亿次了,但越是多说,越在我们身边和心中徘徊不去。说“不必读”者,是因为这三本书,人们不读而已有其说,如果把“传统文化”比作我们朝啜夕哺的羹汤,它们是里边最重要的三种原料。
书乡:“鸢回头”这个书名,是否有何深意在里面?
刀尔登:书名起得随意,而且有点文艺,我是后悔的。鸢是纸鸢,也就是风筝。那几天里碰巧读到一句诗,“若使纸鸢愁样重,也应难上最高头”,便扯来做了书名。大概不少人也像我一样曾经希望和以为自己的想法更独立一些,最后发现并不如断线风筝,脚上的线永远在那里,这时回顾,便如陆游说的“四十年前我,回看定是谁”了。
书乡:在谈孔子时,您说到有趣的一点,说年轻时不大看得上孔子及《论语》,崇尚老子,但现在反倒会觉得孔子可亲可敬。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刀尔登:孔子谈的是日用伦理,家常一些,年轻人大概对这些不大耐烦。老子则“震其艰深”,玄之又玄,觉得一定有大道理真道理在里边。现在觉得,有是有,但没那么玄。
书乡:三部书今天都被当成传统文化的代表,特别是《论语》及孔子,被视为“正统”文化的代表,成为中小学生必读必背书,但另一方面,您也多处谈道,孔子被工具化了、格言化了。我们如今形成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中,很多都是这种工具化了的孔子,与《论语》中那个有点可爱的孔子相去甚远。这种偏差是如何形成的?在今天有可能得到纠正吗?
刀尔登:偏差是源于历史的本性,不必也不可能纠正。背后的问题,我想简单的比附也许是有效的:在拿孔子来化民这一方面,当代与古代的距离,大概能表达当代中国与古代中国在文教、意识形态方面的距离,也就是说,如果孔子学说的功用仍然如古代一样,那说明我们的相应风俗仍然是以国家主导为主,而不是以社会自发为主。
书乡:前言中,您谈到三部书中最推荐《庄子》,说因为其濒危,所谓“濒危”体现在哪里?
刀尔登:《庄子》掺有后学的作品,而且庄子本人也有自相冲突之处,但总的说来,它对当时的权力体系以及价值体系是蔑视、不合作的。在古代,《庄子》的重大意义在于新建一种独立于官方的价值体系,使读书人有另一种精神出路。也是在古代,确实有这样一种体系,但始终是空洞的,士人可以不做官,不谈主流那一套,但在这种新的体系中,也总得做点什么,不能只是喝喝酒写写诗吧,如果没有新的一套知识追求以及因此建立的与其它社会阶层的新的关系,并由此而改变社会结构,那么,这种体系太薄弱了,难以独立。所以我们看到,读书人到庄子书里找找漂亮活,挂在嘴边上,便觉得自己不俗,就像沈约说的,“从宦非宦侣,避世不避喧”,在这里,庄子从一种实践的哲学变成了精神粉饰。
书乡:历来总有论说庄子之学对士人影响很坏,您在书中予以反驳。在您看来,《庄子》是极度的绝望,那么您对庄子的推崇,是否也会有某种悲观的性质在里面?
刀尔登:我想现代人有现代的思想工具,不需要到《庄子》里找出路。当然,包括庄子在内的古代思想者与当代精神有思想史上的源流关系,但处理当代问题,还是要使用当代的思考方式和验证方式,以当代的方式判断得失,然后把经验传递下去。
我谈不上推崇庄子,只是觉得它比别的古书更有生气一些。《庄子》的反抗方式,在今天是失效的,但它所表达的某一种人之天性,不管有没有《庄子》,都不会消失,都会在所有的时代找到表达。所以我并不悲观。
书乡:对于三部书,您都提出说,后世的重重解读、误读乃至曲解,遮蔽了这三部作品原初的真实性和作者的本来意思。不过,在历史形成的这么多误读之下,如何确定什么才是真实性,甚至是否还存在所谓真实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对《论语》《老子》《庄子》,在读原本之外,如何面对其漫长的接受、衍变史,是否需要完全摒除?
刀尔登:还原是不可能的,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可以作为知识之对象的历史本体;至于追求接近原意,是学术性的工作,咱们普通读者大可以不去管它,拿起一本书,喜欢就多看几页,不喜欢就少看几页。古书确实在历代流传过程中,与传统交互作用,接受史是一个专门的学科,我也不懂,只想阅读应该是愉快的事,不该太辛苦。
书乡:书中多次提到,经典自身也是对其产生时代寻找出路而不得的产物,读经典并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既然如此的话,我们读经典的目的是什么,所能从中受到启发的是什么?仅仅是个体修身层面上的吗?
刀尔登: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当代问题”,但因为人类经验的共通,以及人类社会基本结构从古到今没有根本性变化,一些古书,一些我们称之为经典的作品,现在来看还是亲切的,就像为我们写的一样。在这方面,阅读经典的意义之一,是将自己置身于更大的范围,置身于从古到今的人类工作中,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感觉,肯定比孤零零的感觉好,何况经典作品大多是表达得很好的作品,阅读它们有很大的机会获得愉快。
当然了,还有实际的功能,比如社交功能,读几本大洋古,谈话时会显得很有来头——这听起来有点浮浅,但知识之传播对实用动机的依赖,大概要超过对学术动机的依赖。
书乡:读此书,会很明显感觉到您作为一个现代读者的现代眼光,但又能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观照。一个现代人,对待历史留下来的所谓经典的理想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如何让“现代思维”和“历史感”产生理性而不僭越的碰撞?
刀尔登:历史帮助我们理解目前的处境。但在我们自己成为“历史”之类,我们的一切都是当代的。我们的合理性,当然,也来自此刻,我们做的事情影响不了已逝的古人,我们做的事影响同时的人以及后人。
古代有个叫王僧达的人,在自家后院挖了一个大坑,打算杀掉一个人,埋在里面,后来听人劝,没有动手。坑毕竟是自己挖的,决定也要自己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