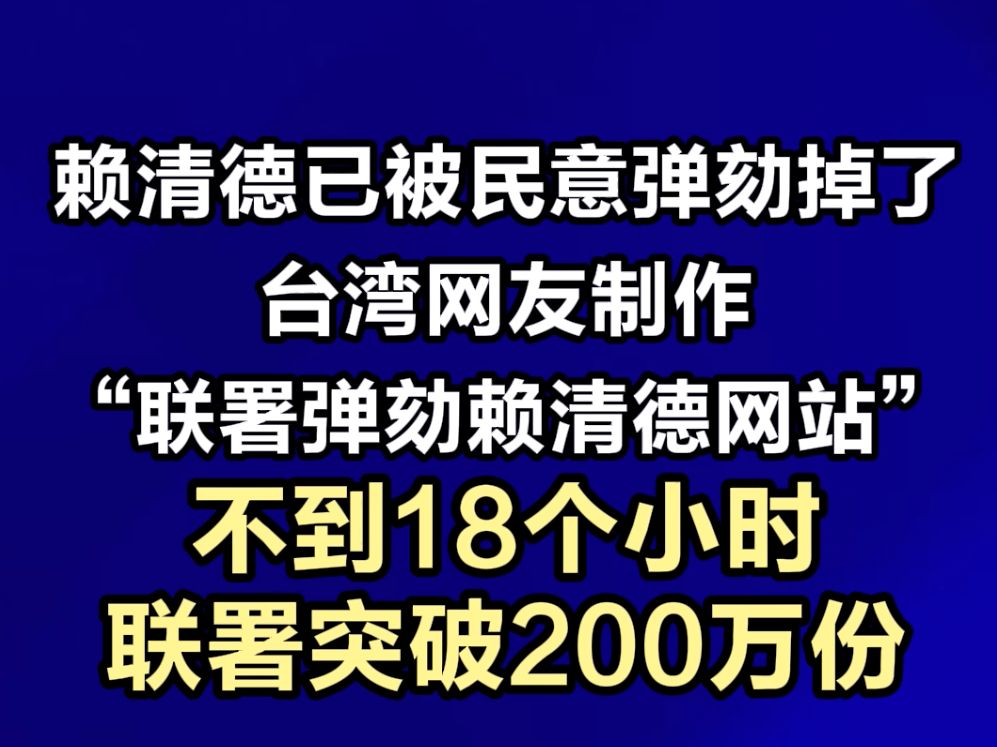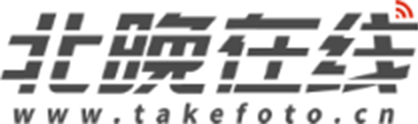濮存昕。
濮存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演员。在四十多年的演艺生涯中,他在话剧舞台上塑造了李白、哈姆雷特、白嘉轩等深入人心的形象,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了鲁迅、弘一法师等一系列极具文化内涵的经典形象,多次凭借高超的演技斩获国内大奖。同时,他热心公益事业,曾担任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无偿献血义务宣传员、中国禁毒宣传大使等,曾荣获“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濮存昕影视作品剧照。

濮存昕影视作品剧照。
我总觉得我在舞台上演话剧就像割麦子,
一天一场戏,八九百观众,
几十场、上百场演出才有几万观众,
真的是一刀刀割,一场场演,生命也一步步走。
北大荒热血少年
我跟着父亲在剧院长大,看戏于我而言和吃饭、睡觉一样,是生活的日常。虽然小时候看戏似懂非懂,但“戏比天大”四个字很早就刻在了我的心里。“戏比天大”,不仅在剧院,也在我家里。父亲在家里是绝对的“太阳”,家里无论什么事,都要以剧院的事、演出的事为中心,都不能影响父亲晚上演戏。只要父亲晚上有戏,家里一下午谁也不能大声说话,他得睡午觉。
我父亲在人艺工作,母亲在银行工作,可家里的话题永远是戏。有一回,我父亲一进门就哈哈笑个不停。笑什么呢?原来那天他在俄国名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演男主角,吕齐伯伯演男爵将军,演戏时吊杆上的灯泡突然炸了,吕齐伯伯吓得一激灵,后半段台词吭哧半天才接上,惹得台下观众一阵笑,甚至到他下次再上场,有些观众还止不住地笑。我父亲在剧院没笑够,回来又跟我母亲学,学着学着又开始笑。这就是演员家庭的生活,好多剧院的乐子会自动灌到耳朵眼儿里。
我在小学是文艺积极分子。毕竟是演员的孩子,在学校里经常演各种小节目,背背诗歌之类的,还参加过北京市少年儿童合唱团。小学毕业后,我进了北京二中的分校——七十二中。这年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时候全国上上下下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达到高潮,基本上我们这届所谓初中生都要离开城市去农村、去边疆。动员会上,我们班报名黑龙江的最多,因为当年三月份珍宝岛战斗刚过,去黑龙江保家卫国多光荣呀。因为腿有毛病,我其实可以不去,但我一直是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干部,就是要去,写了请战书,根本不恋家。我跑到设在灯市口中学(现在的二十五中)的招生办公室强烈要求下乡,人家检查我正步走、蹲下去站起来,还要我写保证书,写就写。很快就被通知准备照片等等,到派出所办手续销户口,每个人能凭票买到一只松木箱子,二十四块钱一只。可惜后来没留下,否则就是知青文物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个被分配的农活是养种马。种马班养马要选个老实有责任心的人,就派我去,做牧马人的日子,天高云淡,自由自在。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我吹着口琴去放马,我赶着马车或骑在马上与下地干活的队伍相遇,我还记得他们那羡慕的眼神。马撒开在草地上吃草,我割完草,找一片干松的地方铺上麻袋,仰脸数云朵。喂饱了马,中午回马厩,我兴许还能抽空睡一小觉。这样的好差事连长为什么会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认真负责的人吧。
牧马人天苍苍野茫茫的惬意生活昙花一现,一年后的某一天我接到通知要被调到文艺宣传队,于是我搭车到了团部。等宣传股庞股长谈话,一直等到五点,他下了班。见了面,他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队,我满心想的是养马,就说“不愿意”。他也许没想到,因为一般人都会愿意离开连队调到团部工作。他说宣传队需要人才,你父亲是著名演员,你一定适合从事文艺类工作,大概是这一类的话。说完他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来的劲儿,连夜赶回了连队。十七岁的我,走了十七里的路,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大自然中独自走那样长的夜路,也是难忘的一次体验。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昼,四周静寂一片,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只有我一个人在原野上走,真可谓披星戴月,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还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从来没有过的安静。这时我遐想林子里藏着熊,躲着狼,也许有苏修特务在搞破坏,我立功的时候到了。第二天,连里表扬我纪律性强,我也觉得自己很有革命精神。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这样,只要听到“共青团员,跟我来”,就能在寒秋季节穿着裤衩往冰凉的水里跳,去捞沤在水塘里搓麻绳用的臭麻。那种艰苦都受过了,何况走夜路?!
在宣传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当了宣传队副队长,正值秋收,已下了雪,政治处把我从连队叫到团里,说:“团里没煤了,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一台文艺节目,到鹤岗煤矿慰问演出。”我说,“一星期哪能排得出一台节目。再说,大家都散在各连里干活呢!”领导说,“不行,这是任务。”见我还有为难的面色,他接着补了一句,“你要是不干,就下连队去。”他说这话口气硬硬的,意思是不听话就离开团部宣传队干农活儿去,我当时没再顶嘴,只用沉默抗议,心里很瞧不起这种官僚。
大家纷纷从各连队回到团部,一起商议六天时间到底能演什么。商议的结果是,排几个新节目,弄几段老相声,最好来个小话剧撑时间。话剧本子从哪儿找?正好看到《解放军文艺》上有个现成的独幕话剧叫《苹果树下》,说的是辽沈战役期间,打锦州的解放军再渴也不吃老百姓苹果的故事。现在想来,那应该是我的导演处女作,也是我的主角处女作,当然,都是业余的,我同时还负责舞美设计和制作。我用木方和豆包布做布景,搭起老乡家的小破房子,用一个网子和细豆包布做苹果树的软景,挂起来的树冠软景接上三合板做的树干,用纸浆做苹果,最后把苹果挂到画上树叶的网子上。可能我当时对布景的兴趣大于当演员的兴趣,整夜整夜地制作布景,累死累活地排练,等领导审查节目的时候,音乐奏起来,我的台词却忘得一干二净,一片哄笑,领导拂袖而去。就这样,鹤岗还是去了,演出也顺利演了。
我是宣传队的,但不会唱歌跳舞,我就做道具。做道具的时候,我还找到了磨炼自己心性的方法。为了节约,我把那些不用的道具上的钉子都挠出来,砸直了,接着用。一大堆钉子,最终都敲直了,搁到盒子里,一干就一天。这类事挺锻炼耐心的,我那时候遇到全团会演,还负责过组织工作,事无巨细,要管三四百号人的吃喝拉撒睡和评比颁奖。真不知道那时候我怎么有那么大干劲,遇到问题只想着解决问题,任务一定要完成,只能用年轻解释吧。
1977年1月,我结束了北大荒的生活,在黑土地的八年,是磨难,也是考验,大喜大悲能增加对人生的理解力和承受力,这对于演员尤其重要,形象中应该有立得住、担得起的气质。北大荒的田垄长得望不到头,割麦子的时候必须一垄一垄、一刀一刀地割,每天腰累得真像折了一般,那种疼痛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也许对我后来的生活与创作有积极的影响。我这人之所以还比较踏实,是因为我有过那段北大荒生活。直到现在,我总觉得我在舞台上演话剧就像割麦子,一天一场戏,八九百观众,几十场、上百场演出才有几万观众,真的是一刀刀割,一场场演,生命也一步步走。
“又出了一个演员”
返城后,经过一番波折,我先考入空政话剧团,后来在蓝天野老师的帮助下,我在一九八六年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九八八年春节一过,剧院开始排《天下第一楼》,我演男主角卢孟实的B角。我在认认真真准备卢孟实这个角色的时候,谢晋导演在筹划请我去拍电影。那时候谢晋导演刚拍完轰动全国的《芙蓉镇》和《高山下的花环》,开始筹拍《最后的贵族》。在这部戏中,我以男主角的身份,第一次为影视观众知晓。平心而论,我不认为自己的表演有多么出色,在首映式上,谢导看着我面对媒体侃侃而谈,在一旁得意地说了一句:“又出了一个演员。”谢导爱护演员是出了名的,从他手上培养的大明星很多。能得到他的赞许,被他器重,我很欣喜。谢晋导演是把我真正领进电影界的引路人。
转年,谢导马不停蹄要拍李凖老师创作的电影剧本《清凉寺钟声》。当年家喻户晓的老电影《李双双》就是李凖老师创作的。《清凉寺钟声》讲的是日本二战投降后,日军、日侨撤退,留下一个孤儿,河南农村大娘将这孩子抚养长大,取名狗娃,孩子有慧根,长大后出家当了和尚,戒名“明镜”,多少年后成了大法师,随代表团访日认母的故事。谢导再次向我发出邀请,让我演明镜法师。
《清凉寺钟声》是1990年10月开机的,先在河南辉县太行山最深处的一个小村庄拍摄,后来这个村子因电影的拍摄改叫了乳泉村。那时候,我和被邀来演老和尚的朱旭老爷子都上了太行山,我们俩分在一个老乡家住,同住一屋,每日从组里的食堂打饭回来吃。老乡家的饭是当年的新粮,馍和烙的饼真叫个香,比剧组食堂的面鲜,可老乡却觉得我们城里饭好吃,于是我们常对换饭食。新粮有营养,没几天,不少演员都胖了,谢导紧急通知所有演员要减肥,要不就没法拍苦难岁月的戏了。我倒没胖起来,但是心真正闲下来了。那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在,而且是和有趣的、看着我长大的前辈在一起。我有时陪朱旭老师喝一小口当地酿的土烧酒,有一次看村里小卖部有种特曲牌子的酒,想换贵点儿的酒解解馋,没想到喝完头疼,又喝了一次,还是有不好的感觉,一问化妆老师,他也喝了,感觉也不好,我们才认定是假酒的罪过,还是喝本地小烧吧。我们还一起聊天、写写毛笔字……一段难得的清静日子。我们俩每日早起去爬村外的山岗,隔几步蹲在山坡顶的小树丛边“方便”,一边自个儿舒服痛快着,一边欣赏山色,看着朝阳的光慢慢扫进山沟里的村庄,炊烟从一家一家灶台烟囱里袅袅升起,被光染成一片金黄透过树梢。一会儿看见这个出门洗漱,一会儿看见那个进后院儿倒尿盆,谁能想到有人在山上俯瞰大地窥视他们呢?还真有点儿神仙在天的感觉。其实大师们写经典,导演们拍力作,演员在领悟角色的生命意义、思想言行的时候,要有如此的视角去俯察、发现。在山下人堆里深入其中那是体验,还要有鸟瞰的视角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演完谢晋导演这两部电影,很多观众认识了我。高亚麟有一次说,那段时间他有一个朋友从外地来空政,无意中瞥见我在院里跑步,她疯了似的冲回房间打电话:“你知道我见到谁了——濮存昕!”
登上“白鹿原”
就这么到了2003年,我刚刚担任人艺副院长,我跟人艺的林兆华导演商量创作什么作品,他说:“咱们得弄一部大作品,排《白鹿原》。”真是不谋而合,我想的也是这个。我还记得那晚聊得有多兴奋,茶喝多了,回家一夜没睡着,失眠了。我们马上联系陈忠实老师,一拍即合,陈忠实老师爽快地答应了。话剧《白鹿原》就此提上了日程。很快我们就和陈忠实老师签了三年的合同,三年内出话剧作品。
长篇小说《白鹿原》有六七十万字,太丰满了,把它改编成三个小时以内的话剧,当然很难,而且我们要用全章本,剧本改编用了两年,再不定稿合同要到期了,别的剧团也在抢这个题材呢。林兆华和原总政治部话剧团团长孟冰最终使剧本有了些眉目,于是五月我们就开始建组,去了西安体验生活,去了五天。
哇,“原上”原来如此。“原”就是西安市向东不到十几里地,突然间断崖式出现一片高地,下面是西安市,上面是原上,地壳运动真是神奇。原上是一片片的村庄,这是黄土高原文化最核心的地方。我在原上的几个村子体验生活,留意寻找白嘉轩的模特。为了演白嘉轩,我得在心里模拟一个样子。这个样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到罗中立画的《父亲》,那端碗的粗粝的手,但那个形象是平面的、固定的,我找不到白嘉轩说话走路、待人接物的动态。见了村民、村长、乡长、书记,都找不到影子,最后在陈忠实老师请人艺全体人员吃烤全羊,对面坐着喝酒吃肉时我猛然发现,白嘉轩的形象就可以是陈忠实老师呀。
体验生活这件事情不太好说。音乐家、舞蹈家去采风,也许直奔主题能找着感觉。但是表演艺术创造角色不一样。我这两年看人艺于是之老师的创作笔记,他曾经写过,他演《龙须沟》的程疯子,去体验生活中找穷苦人的样子。他要演一个工厂的厂长,可是采访工厂的厂长后也没“找”到戏里的厂长体验对象,费半天劲也没有一点儿收获。
我们决定用陕西方言排《白鹿原》,所有演员都要说陕西话,我的陕西话主要是跟郭达学的。大伙为了贴近生活,努力学方言,就是在萃华楼请陈忠实老师吃饭,还向他求教怎么发音准,一片笑声,引得别桌的人直瞧我们这一桌。宋丹丹当然有语言天赋,说我太差,又问我:“你有车吗?一会儿坐你的车回剧院吧。”我答应了她。等吃完饭走出门,她发现我的是自行车,夸张地说:“这也是车!太逗了。我二十多年没骑过自行车了,更甭说被人带着了。好吧,坐‘二等’。”最后这“二等”是北京话,也许老式年间等到汽车是“一等”,没等着汽车,让叫跑活儿的自行车代步叫“二等”。我骗腿儿上了车,她抱我腰上了后座。路上有行人惊呼“宋丹丹”,她还招手咯咯乐。说方言确实让这出农村戏有了品质上的提升,接近了生活真实,但演员一时半会儿音调还容易拌蒜。
《白鹿原》戏里面的魂儿、面貌上的神儿绝对是来自华阴的老腔民间艺术家。当年在西安原上体验生活时,五月天热,这天吃完午饭大伙儿正犯困,陈忠实老师请全体人员听高原风情的民间艺术演唱,秦腔、“迷糊调儿”、碗碗腔先唱,最后是从华阴请来的老腔。小舞台上一声吼,敲板凳的叭叭响,我们这些打盹的一下子全醒了。民间艺人们扯着嗓子喊出的唱腔让林兆华一下子笑了,他回过头,手掌拱着嘴向我也吼了一句:“有了!”他脑子里一下子形成了用老腔、秦腔串联起十多个戏剧片段的舞台结构,将戏剧人物抑郁在胸的情绪面向天地吼出来。后来所有观众一提北京人艺的话剧《白鹿原》,马上会记起老腔的演唱。后来我们在话剧演出的休息日,还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举办了“老腔专场音乐会”。观众中,在京的“陕西乡党”来了很多,就想听乡音。我为音乐会当主持人。老腔民间艺术当时已快失传,年轻一代没有人愿意学,我们的《白鹿原》让老腔一下红火了,央视《艺术人生》也办了专场节目。我因此与这些民间老艺人交情很深。他们的朴实、善良、对手艺的忠诚,还有说话的硬朗、实在,掷地有声的方言,眼睛里与人交谈的认真劲,都是我饰演白嘉轩获取角色感觉的源泉,使这个角色与我扮演的其他角色大不相同,突出了性格化的塑造,我真感谢他们。
2021年我们安排了《白鹿原》的演出,领唱张喜民领着他们一干人来京,在酒店隔离了15天,每顿饭分派两三个人来人艺食堂打盒饭在酒店吃,他们还有内部纪律,不喝酒,不准个人向人艺提要求。他们后来又参加排练了十几天,结果疫情又严重了,只能退票,不带观众,内部拍摄演了一场便回了陕西。我没听到他们一句怨言。他们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情绪,我想到“风来穿衣,雨来打伞”的佳句。我特地赶来剧院为他们送别,分别时只有不舍。希望在他们还不老,在我也还有体能的年月,再请他们来京吼起老腔,再演《白鹿原》。
陈忠实老师的《白鹿原》深受《静静的顿河》的影响,这两部作品都既有文学巨作的体量,又有文学语言、故事的精致。俄罗斯的八小时话剧《静静的顿河》我看了,演员没有问题,导演也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淡化了时代背景,总体给人的感觉就变成了偷鸡摸狗的男女之事。相比之下,我们的《白鹿原》真的不差,而且我们的文学剧本是全章本的。文艺离不开男女情爱,离不开人的本性张扬,但是要有社会属性,我们中国的戏剧不仅要追求很个人、很私人的趣味性,更要着意于深刻的、社会人间的思想内涵。
就像诗人食指在《相信未来》里说的,用“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陈忠实老师不受干扰地凭直觉对待土地文化在时代中的变迁,对待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高原上的中国近现代史。他写到了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写到了恋爱自由、进步、参加革命这些新的文明,写到了选择不同道路、不同生活方式的孩子们,写出了一条既一泻千里又鱼龙混杂的黄河,写出了愚昧与文明交融的混沌的世态炎凉。
还想演《白鹿原》,还愿演“白嘉轩”……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