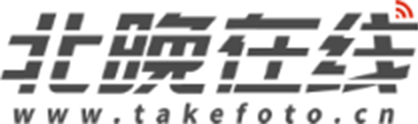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结束后,开始群众游行。
群众游行分多个方阵进行,其中“致敬”方阵由21辆礼宾车组成。当礼宾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时,车上一位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满头白发的老兵,向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郑重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军礼。
他就是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东南宋村的刘贵年,是“致敬”方阵中的30多名老兵之一。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刘贵年
从小兵到老兵
“我以为,有吃有穿就是好日子,可是没想到这么好。家家吃得好,穿得好,住得也好,还有土地。”
2021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三,我再次来到东南宋村拜访这位老英雄。
上午9点,温暖的阳光穿过尚未发芽的香椿树,照在老刘家的窗格上。我推开虚掩的门喊了一声“老刘”,却不见人。
躺柜上的电视机正演《亮剑》,李云龙的骑兵连正举着马刀向敌人冲去。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屋子里一片厮杀声。
老人哪里去了?我正欲到院子里寻找老人,忽然看见他在里间洗脸。
老人93岁了,脸色红润,腰板挺直,穿着黑色羽绒衣,黑裤子,黑棉鞋,和村里的普通农民没有两样,慈眉善目,满脸和蔼,没有丝毫强悍之气。
老人也看见了我,笑着对我说,你先抽烟,我一会儿就洗完了。
在等老人洗脸的工夫,我环视了一遍四周,见老人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外屋两间,大锅,大炕,炕上铺着花布。两床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地下摆着一张方桌,一张沙发,一只大躺柜。躺柜的正中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纪念”圆形水晶杯,杯座上写着“老兵方阵 刘贵年”字样。
参加国庆游行的老兵有30多人,山西省有3人,忻州市只有刘贵年一人。那天,他举起右手,五指并拢,向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他说,“快70年没敬军礼了。虽然胳膊没有年轻时那样灵活,可是,我敬得很用心,和当兵时一般的。”
我问他敬礼时想什么?
他说,“什么也没想,就想敬礼。向国家致敬。”
老人收住笑容,满脸严肃,再不说话。但是,我看见他胸脯起伏,目光凝重。他想起了自己冲锋陷阵、浴血奋战换来的共和国安宁,想起自己与国家的血肉关系。
见老人心情沉重起来,我改了个话题问,吃了早饭没有?
“吃了。过年的东西还没有吃完,馍馍、花糕、蒸肉,什么都有。”
“现在的生活好吧?”我问。
“好!”老人又笑了起来,非常满足地说,“好得不能再好了。”
“打仗时,想到这样的好日子没有?”
“打仗时?”老人缓了缓说,“打仗就是为了好日子……可是,没想到这么好。”
刘贵年出生于1930年9月。他爷爷是刘家山人,穷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来东南宋给李财主种地。“打下粮食以后,三股子分粮,财主分三分之二,种地的分三分之一。”就这样,他爷爷给李财主种地,他父亲给李财主种地,刘贵年小时候也给李财主种地。
老人的父亲叫刘丙荣,成亲时还住在地主的场院里。母亲叫刘成枝,是个后婚,带着一个儿子,后来那个儿子被他奶奶接回去了。
刘贵年8岁那年,看见别的孩子上学,就偷偷跑到学校念了一天书。没想到一回家,父亲就问他做甚去来?他说念书。父亲一听就火了,说咱这家庭还念书?不行!明天跟我干活去。刘贵年不敢反抗,第二天就跟上父亲去地里挽草、薅苗子。10岁就跟上父亲锄地,父亲锄两垄,他锄一垄。
他说,我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兄弟。一开始粮食基本够吃,后来人口多了,就不够吃了,饥一顿饱一顿的。
“国家闹好了。”老人笑着说,“当兵时,政委说,要让受苦人都过上好日子。我以为,有吃有穿就是好日子,可是没想到这么好。家家吃得好,穿得好,住得也好,还有土地。”老人笑了,笑得真实、淳朴、满足、灿烂。
老人所说的“闹好了”,是忻州方言,是做好了、干好了、搞好了的意思。
我忽然想起,老人从北京回来以后,就曾经说过这句“闹好了”。当时,我以为他说的“闹好了”仅仅是指盛大的庆典,不知道包含这么多的意思。于是就接着问,你说国家哪方面还闹得好?
“武器。”老人忽然兴奋起来,“你看阅兵时那新式武器,可多了,我都认不得了。”说起武器,老人又和当年比较起来。
1947年2月,晋绥军到处抓兵,区小队的周万元怕他被晋绥军抓走,就动员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游击队的枪不多,队长只给了他两颗手榴弹让他背着。那年他17岁。第二年春天,区小队编入忻东支队。连长给了他一支枪,可他个子小,背上枪枪托子还拖地。连长没办法,又给了他两颗手榴弹让他背着。解放忻州时才给了他一支缴获下的马窜子枪。
忻州解放后,刘贵年被编入西北野战军1纵队7旅19团二营1连,给连长当通讯员。紧接着就是打太原。
他说,解放太原最难打的是牛驼寨。敌人有枪有炮,还有明碉暗堡,可是,咱的部队连子弹都不够用。一个兵只有10发子弹,一挺轻机枪只有50颗子弹。只有等敌人靠近了才能打,或者是与敌人拼刺刀。解放太原后,缴获了很多武器。战士们不爱别的,就爱子弹手榴弹,欢喜得一人背了一身。说到这里,老人呵呵地笑出了声,胜利的喜悦霎时荡漾在脸上。
牛驼寨地处太原东山,地势陡峭,沟壑纵横,是阎锡山重兵把守的“四大要塞”之一。敌人工事完善,补给充足,易守难攻,“拿下牛驼寨就等于拿下太原的一半”。
刘贵年说,我们的口号是“要想解放太原城,首先解放牛驼寨。”18团和我们19团负责主攻任务。500多人的18团二营,打得只剩下27名伤员了。我们19团二营又增援上去。战斗打成了拉锯战,山头被敌人夺过去,我们又夺回来,一晚上冲锋了12次。牺牲了一队再上一队。打到最后,山上尸体摞着尸体。我们二营牺牲了100多人,受伤200多人。
老人的脸上没有了笑容,思绪完全回到那场残酷的战斗之中。
“周润万就是打牛驼寨牺牲的。”老人说,周润万也是东南宋人,和我同岁。他是师部的通讯员,我是连部的通讯员。师长到前沿检查阵地,我和他都进了窑洞。我坐在里边,他坐在外边。恰好一颗50型炮弹打进来,把他的右腿炸断了,左腿也只连得一点点了。我急忙叫来护士给他包扎好,让担架把他抬到医院。结果,还没到医院,就在半路上死了。
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一场攻坚战。解放军伤亡4.5万人,其中打牛驼寨就牺牲了5000多人。
刘贵年说,1949年4月24日凌晨,攻城部队用1300门火炮对太原城发起总攻。我们冲进城,可是三排没跟上来,连长让我去找三排。大家都往城里冲,我却往外跑。子弹打在脚后跟周围,噗噗地直响。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三排,返回来时,城里很乱,好不容易才找到部队。这时候,三排自己找回来了。原来他们已经跟着其他部队进城了。
太原解放后,刘贵年所在的部队只在太原呆了一天,就转战大西北。饿了吃干粮,渴了喝河里的水。4个月边走边打,先打陕西,然后打兰州,直到1949年9月5日解放西宁。
在兰州,刘贵年当了营教导员杨兆通的通讯员,后来杨兆通当了团政委,他又当了警卫员。
峥嵘岁月
“怎么不去?只要国家叫我,我就去!”
电视机里的厮杀声仍然在响着。我越来越理解了刘贵年为什么喜欢看这种片子。因为这种厮杀声已经渗入他的骨髓,融进他的血液,成了他的人生底色。
我看了一眼电视机,看见李云龙舍不得让政委赵刚调走,两个一边喝酒一边争吵。老人以为我嫌电视机声音大,就把声音关了,一边看无声电视,一边讲自己的故事。
“杨政委培养我入了党。”提起杨政委来,刘贵年首先想起入党的事来。
1950年刚过春节,杨政委问他多大了?
他说,20岁了。
杨政委问,你想不想入党?
他说,想。早就想了。
杨政委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写申请?
他说,我没文化,不会写申请,又怕自己不够格。
杨政委问他,你知道打起仗来,哪些人冲在最前头?
他说,冲在最前头都是党员。
杨政委又问,你敢当先锋吗?
他说,我敢当先锋,绝不落后!
杨政委说,你够格了。入吧!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血与火的战争考验每一个战士,更考验共产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刘贵年所在部队是炮团,离前沿较远,他又是团政委的警卫员,相对而言,牺牲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绝不意味着没有考验,绝不意味着不需要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
195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刚吃过午饭,天突然下起大暴雨来。山洪暴发,营地存放的军用物资被洪水冲进河里。团长下令警卫连抢救物资。刘贵年带头跳到洪水中。前两趟,河水刚至肚脐,还能把物资抢上岸,不料第三次下水时河水暴涨,从腰间漫到胸脯上。刘贵年等20多人手拉手站在洪水中,不料,一排墙头高的大浪汹涌而来,漫过头顶,20多人一下就被洪水冲走了。团长下令全团救人。晚上11点左右,战友们在几公里外的马市上的马槽旁发现了浑身是伤、两耳灌满泥沙、昏迷不醒的刘贵年。战友们把他背到医院,七天七夜才抢救过来。
自此以后,刘贵年的耳朵经常难受。他闺女说,参加国庆阅兵的前几天,父亲的耳朵忽然听不见了,急忙去忻州医院看。医生从他耳朵里掏出了3块红色的泥块。——可能是那次洪水灌进去的泥沙。
老人没有听见我们议论他的耳朵,却继续着他的思路说,“党员就要有党员的样子。就得当先锋。”
丰碑用热血铸就,生命靠信念支撑。从举起拳头宣誓的那一刻开始,刘贵年就在自己心里建起一个信念,刻下一个标杆,历经70年的生死风雨,仍然坚定不移。
1951年,刘贵年所在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军一师炮兵团,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最前线。
说起炮兵团,老人清楚地记得,“上级给了我们团90辆汽车,还有榴弹炮。一门炮7个人。一颗炮弹80斤,能打40里。”
改为炮团以后,刘贵年立过三次三等功。
第一次立功是1952年。那一次,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的轰炸机5分钟就轰炸一次。他跟随杨政委上前线视察,忽然一颗炸弹掉在他们身边,他猛扑上去将杨政委按在身下。炸弹爆炸了,把他身上埋了厚厚一层泥土。杨政委问他伤着没有,他耳朵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见。政委扒掉他身上的泥巴,他爬起来先晃了晃胳膊,又晃了晃腿,都没事。看见“那个弹坑有一米多深,周围全是三尖八脑的弹片”。
“你真勇敢啊!”我赞叹道。
“我是警卫员,保护首长是我的责任。”老人似乎在讲别人的故事,脸上非常平静,还带着微笑。
我曾向村里人打听过刘贵年的事情,人们只知道他当过村干部,没听说他当过兵,更不知道他曾在战场上立过三次功。老人的大儿子告诉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的人,而且性情温和,一辈子不发火,不骂人,不打骂孩子,不和老婆吵架。但就是这个从来不着急的慢性子人,竟然在生死关头,纵身一跃,用自己的躯体保护别人,用自己的死换取别人的生。这不就是他说的“党员的样子”吗?
“你真是个英雄。”我不由得感叹道。
“我不是英雄。”
“那谁是英雄?”
“周润万、李功成、副政委,他们才是英雄。”
老人说,李功成是在西宁抢险中被洪水冲走的。等大家找到他时,他头上碰下个大窟窿,两腿陷在胶泥里拔不出来。周润万、李功成,都是东南宋村人——我们一起参军的三个人牺牲了两个,就留下我一个了。
说完李功成,老人又说副政委。他说,那是1953年,在朝鲜马连山。有一天夜晚11点左右,团部领导都在山洞里开会,结果被敌人发现了——可能是敌人看见卫生员在河里洗衣服从而发现了我们——敌人的飞机在头上飞过来转过去,炸弹像雨点似的往下落。山洞轰隆一下被炸塌了,我们20多人被埋在山洞中。
战友们在外面冒着雨朝里挖,我们在里面往外挖。我们没有工具,只能靠手挖。我的双手磨得血肉模糊,又憋得上不来气。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挖出去,保证首长的安全。后来由于缺氧,连蜡烛也点不着了。没有蜡烛,我们就黑着挖,直到第二天下午5点多,山洞才挖通。我们被救出来了,可是副政委被憋死了,才38岁。
老人满脸肃穆,没有流泪,没有哀伤,默默地看着窗外,半天才说:“可惜他们没见国家闹得这么好,没过上好日子。”
见老人心情沉重起来,我忙问他身体怎么样?
他说自己“身高1米68,体重117斤,除了耳朵有点背,一切都好。”
“你当兵9年,出生入死,没有受过一点伤,真是个福将啊!”
老人却淡然地说:“活的是时气,死了也光荣。”
见他这样说,我干脆问,如果还让你当兵,你还去吗?
“怎么不去?只要国家叫我,我就去!”老人忽然满眼激情,一脸豪气,平日那种温和慈祥之色荡然无存。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不麻烦国家
打仗就当兵,不打仗就当农民。这就是刘贵年的选择。
太阳越来越高,温暖的阳光洒满小院。院内一株老枣树苍劲挺拔,大约有一百多年了。院落四周的香椿树即将萌动新芽。东南宋村的香椿芽绿中带红,风味独特,在周边十里八乡颇有名气。
刘贵年住着三间平瓦房,看样子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老式方格窗上糊着白纸。柱子上贴着红春联,房檐上吊着红灯笼,春节的喜气仍然弥漫在院子里。
1955年2月,刘贵年从朝鲜回国,然后回到离别七年的东南宋村。
他说,我申请复员,政委不让走。有三个工作让我选。要么去警卫排当排长,要么去汽车排当排长,要么去东北炮校学习,然后当连长。我说,“我没文化,当不了干部,也不想给国家添麻烦。我想回家当农民。”
老人说,政委对我可好哩。在朝鲜时,士兵每月津贴4块钱。团长政委每月津贴70块钱。政委不管钱,让我保管着。那年,我母亲写信说,家里困难,让我把旧衣服旧鞋捎回家。政委看了信,知道我家困难。我立了三等功以后,部队奖励了100块钱,政委还用自己的津贴添了100块钱,给我邮回家。母亲收到钱,欢喜地来信说,原来家里有一头牛,现在又用你邮回来的钱买了一头黑定定的毛驴,给人代耕地,有了收入。复员时,政委说,把我的钱全拿上,家里的东西你爱什么拿上什么。可我怎么能拿政委的钱和东西?政委不过意,就把自己手上的罗马表给了我。
刘贵年抱着“不麻烦国家”的心理回到村里,先在粮食局扛麻袋,后来到太原预制场干活。1964年村里选大队长,五个候选人中刘贵年得票最多。从此,在大队长、管委会主任、村委会主任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直到上级号召农村干部“年轻化”才退下来。
东南宋也叫小南宋,位于忻府区城东南8公里处的丘陵地区。清末民初,村里人大多走“北路”做买卖,赚了钱就修门楼、盖房子,所以有“砖瓦圪洞小南宋”的说法。这些买卖人结伴回家,又结伴离家,所以,又留下广为流传的一句歇后语——“小南宋养娃娃——一乍子”。
东南宋村北是平地,村南是坡地。祖祖辈辈靠天吃饭。刘贵年当村干部以后,带领全村人修路植树、平田整堰,打井修渠,后来又实行“生产责任制”。他说,“党员要做建设社会主义的顶梁柱。当干部不能贪污浪费、多吃多占,要起好带头作用。”
“不能贪污浪费、多吃多占,要起好带头作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党对农村干部的基本要求,时间过了这么多年,刘贵年还能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可见这些话在心里铭记得有多深多牢。
我问他,“回到农村后悔不后悔?”
他说,“不后悔,我是自愿的。”
我又问,“当兵好还是当农民好?”
“都好。”老人笑着说,“当兵时,只要不行军打仗就想家,可是回到村里,又经常梦见部队。”
打仗就当兵,不打仗就当农民。这就是刘贵年的选择,也是他“向国家致敬”的人生轨迹。
谈到这里,我想从墙上挂着的相框里找几张记录刘贵年人生轨迹的照片,却看见一张他和妻子结婚时的合影。他身着绿色军装,胸前戴着奖章。妻子梳着长辫,穿着淡粉色碎花衫子。
“你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我问。
“复员那年结的婚。”老人说,妻子叫王全灯,双堡人。当年,他一复员,就有许多人给他介绍对象。他看中了王全灯。部队给的300块钱安家费,正好娶媳妇。20块钱彩礼,70块钱买衣服,剩下的办喜宴,全够了。
老人看着相框,声音忽然低沉下来,“老婆走了8年了。得了急性心肌梗塞,抬到医院也没抢救过来,前后不到5个小时就走了。活了75岁。”
老人的大儿子说,我妈走了以后,父亲天天一起床就在我妈的遗像前点一支烟,供一杯水。晚上睡觉前再点一支烟,供一杯水。中午供饭菜,还点一支烟。八年了,天天如此,没有忘记一次。
“她活着时好抽烟。”老人说。
这时我才发现里间有一个旧橱柜,橱柜里摆着一张遗像。遗像前有一杯水,两个碟子。一个碟子放着新鲜的饭菜和一双筷子,另一个碟子里竖着一支燃烧的香烟。一丝青烟袅袅上升,静静地散发在房子里。
“无情未必真豪杰”。看着这位耄耋老人,我明白了什么才叫情,什么人才是英雄豪杰。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岁月冲刷不了英雄的光芒,平凡更显英雄的价值。
“英雄者,国之干也。”时代进步离不开那些光彩夺目的大英雄,但能站在历史高地的大英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英雄恰恰是那些默默无闻而终生“向国家致敬”的人。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张来元
流程编辑:U022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