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七世纪的盛唐相遇:女性摆脱了礼教的羁绊,获得更多自由
在撒马尔罕的康国故城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我看到三幅壁画。它们已斑驳得有些模糊不清,却与敦煌壁画的色彩和笔触遥相呼应。
作者:蒲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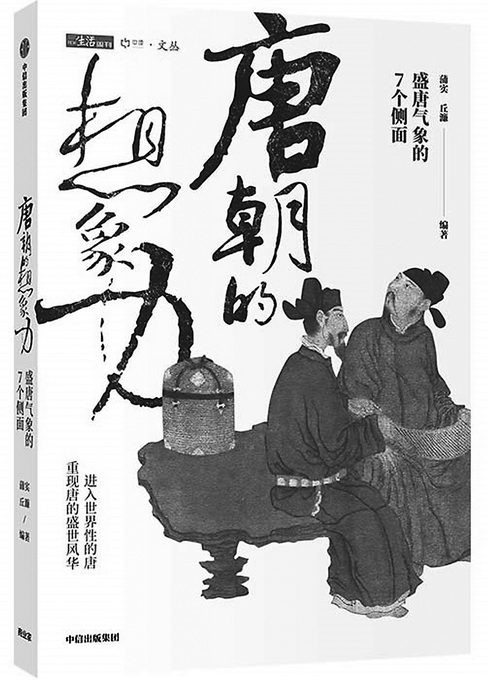
第一幅画中的人身着唐装,头戴唐初盛行的幞头,身着窄袖长身袍,系腰带,垂鞶囊,佩长刀,有人手托三叠,有人手托丝,显然是一幅献礼图。第二幅是唐装仕女的泛舟图,一艘凤舟上有几名女子,发髻高耸,一位贵妇正被五名贵妇簇围着。第三幅则是唐装骑士的猎兽图。
那时我刚乘了好多天火车与汽车,穿越了时而壮美、时而荒凉的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撒马尔罕郊外那处鲜有人至的遗迹处,与七世纪的唐朝相遇了。唐朝的文物制度曾传播到中亚腹地的深处,还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是中古极盛之世。
唐朝盛世的气质可以用很多词语来形容。它的疆域辽阔壮美,它的诗歌浪漫奔放,它的心态自信雍容。当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英姿飒爽的胡服女骑俑,在新疆博物馆看到阿斯塔纳墓出土的活泼飞扬的儿童图时,我感受到了这个朝代涌动着的健壮生命力。除了马球壁画,武惠妃棺椁上的一幅驯兽图,则向我展示了唐人骁勇善战的男性气概:很可能来自异域、蓄着长胡子的驯兽师正在赤手与形如雄狮的巨兽搏斗。这样的图景,我曾在帝国版图蔚为辽阔的波斯帝国(今伊朗)首都波斯波利斯的浮雕上看到过,它象征着帝国征服者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勇猛豪迈的气魄。
在这个世界性的国家里,唐人如何看待自己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一个唐人身处何种世界观念和时代精神中?形成他们开放包容心态的源头又何在?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引用朱元晦语“唐源流出于夷狄”,并指出种族与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
唐与隋的皇室实出同一个政治集团,统治基础相似,继承了鲜卑游牧民族的传统,融合了五至六世纪统治华北边境的“蛮夷”文化。这一血统和文化上的起源,几乎决定性地影响了唐人的世界观。
与正统的儒家天下观并不完全相同,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皇帝提倡包容性,认为所有民族最终都将纳入中国,他们的帝国理想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游牧民族,异域外来者也可以融合,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
唐人在文化观上是汉民族的文化观,以天朝上国而自居,骄傲于自己的典章制度和华浮文采,但对外来文化从来不排斥和抵触,奉行拿来主义,兼收并蓄。借鉴自中亚的金银器制作技术就是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发展的。在这个儒家文化还没有全面渗透人们精神生活的“历史缝隙”里,唐朝人没有太多的思想束缚,也许正因如此,唐的文学才如此快意恩仇,唐的精神气质才如此奔放飞扬。
唐以它的自信放开怀抱迎接各国使者,胡商、遣唐使和留学僧纷纷来到长安,在鸿胪寺、国子监和西市留下足迹,胡风唐韵融为一体。长安不仅是商业枢纽和物质汇聚之地,也是达官贵人、才子佳人生活的空间。那时的文人,无论见面、分别、宴会、游边、隐居,都要写诗。作为一个开疆拓土的扩张性国家,唐朝很多诗人投笔从戎,写下许多边塞诗。
唐长安也是“信仰之都”。波斯的商人带来景教、祆教和摩尼教,从印度、中亚而来的佛教僧侣,把到达长安视为登上传法事业的顶峰,而来自东瀛和新罗的学问僧们,又把长安的佛学传播到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上。唐的出使者玄奘、鉴真和义净,则在他们留学、传教和翻译著书的活动中,扮演了大唐黄金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开始南移,不仅是运河,帝国的道路网络也从北方边疆扩展到南方,把帝国的西南和东南沿海部分连接起来,番禺、扬州、益州都是富庶繁华的城市。
唐朝也是一个“她世纪”,女性摆脱了礼教的羁绊,获得了许多自由,也出现了武则天这样的女性人物。在唐朝建立14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想要再次进入世界性的唐帝国,从城市、宗教、诗歌传奇、出使者、外来者和女性等多重视角,来领略它的盛世风华,以梦回大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