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神堂记忆》:看曲阜孔氏是如何通过修谱度过世纪难关的
上世纪初,封建旧制度被推翻,曲阜孔氏面临其官封祭田极可能被新政府没收的巨大危机。曲阜孔氏遂决定承认散居外地的孔姓者的孔子后裔身份,并联合全国孔姓人家撰写孔氏族谱。修谱,这一意在扩大宗族政治影响的举动,带给散居全国各地的孔氏一种特殊的荣耀。
作者:朱悦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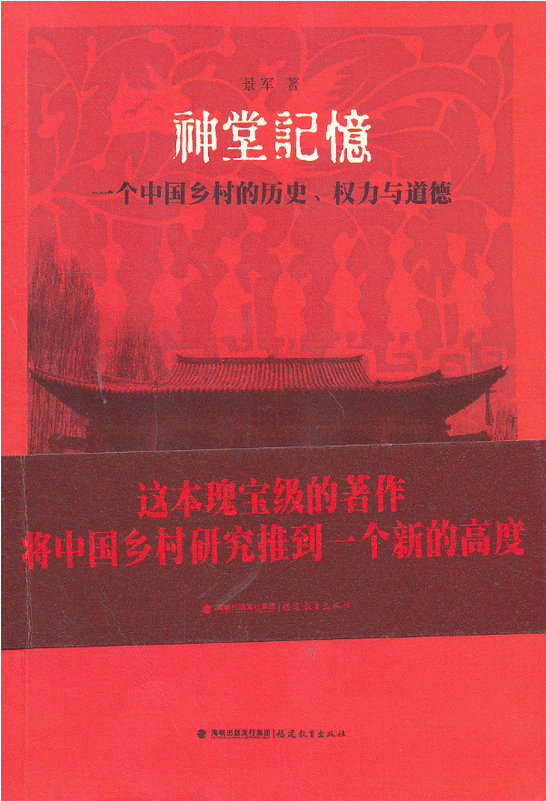
《神堂记忆》 景军 福建教育出版社
及至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来到甘肃省大川村进行田野调查时,这种因得到曲阜孔氏认同而声望倍增的荣光,依然没有丝毫褪色。
在景军的描述中,大川位于兰州附近,是一个孔姓人家聚居的村庄,村里也有不多的外姓人。大川孔氏将自己的来源直接追溯到孔子,并在村里建了一座规模不算小的孔庙。在1949年以前,这座孔庙是大川村及附近22个村庄共达两万人的祖先崇拜中心。
后来,这座孔庙被摧毁了。
戴眼镜、背破书包的景军来到大川时,大川孔氏正准备修复孔庙,并编纂一部祭孔的仪式书。那正是改革开放后,大川人的脸面刚刚变得油光的时候。
这种传统文化制度的复苏,并不早于中国社会的平均值太多。据有关专家介绍,当下兴盛的“修谱热”就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不少家族不惜重金,耗时十几二十年修谱,而且绝大多数并非名门望族,不过是平民百姓。据说,上海图书馆的家谱阅览室近年获捐的新家谱连年走高,每个月都能收录20到30种。
奇怪得很,中国人似乎总是一方面越来越现代,一方面越来越传统。细想之下,也不奇怪,“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本就是终极哲学命题,而一部族谱至少回答了其中两个。
在对大川孔氏修复孔庙的观察中,景军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1905年所修的族谱,还是1991年编纂的仪式书,都对不利于祖先名声一些史实进行删除、回避或改动,制造出一个神话,说当年来到西北的大川孔氏的始祖不仅是个爱国者,而且是捍卫国家尊严的民族英雄。
此外,1991年完成的仪式书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很正式的文风、深奥难懂的语言,以及仪式器具的复杂名称”构建了一个仪式参与者似懂非懂的指导蓝本,从而建立庙宇和典礼的权威性。正如景军所说,“一种古奥和神圣的语言,与世俗世界区分开,暗示了仪式和仪式词汇是忠诚地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因而象征了正统和权威。”
这就是记忆的建构。
社会记忆有集体记忆、官方记忆、民间记忆三种研究取向。民间记忆则受限于个体生活经历的局限,而呈现出“盲人摸象”的状态。而集体记忆本就是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在往事的提取和复刻过程中,产生后辈为先人避讳、先人被后辈神化的现象就再正常不过了,毕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谁是我最亲近的人”等一系列问题的中心,都是“我”。或许,在修谱这件事情上,最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基因传承、血脉相连的感觉。
当然,修谱这看似很传统的行为,也正在融入现代性的因素。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些家族修家谱不再“重男禁女”。2018年春节期间,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甘丽华就其亲身经历,详细记录了这种变化:“在这次修族谱中,女儿第一次被允许独立‘上族谱’:以前的老谱里,女儿只会出现在其父亲的名下,新修的谱里,女儿也有独立的一栏,既介绍其‘来处’——如其祖其父,也会说明其‘去向’——嫁至何地何人。”这种新的时代特色,可能使家谱族谱成为血脉相连的更完整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