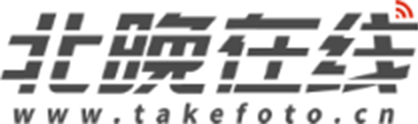他不仅是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

裴文中(1904—1982)

1929年,裴文中抱着包裹好的“北京人”头盖骨。拍摄者由于太注意头骨化石而忽略了裴文中的头部。

“打格画方”的发掘方法沿用至今。

1957年,裴文中(左三)等在广西柳城巨猿洞。

裴文中在工作。

裴文中大学时的照片。

1931年,裴文中(左)、翁文灏(中)、法国专家步日耶在北京周口店。
裴文中(1904—1982),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者,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地层学的奠基人。
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名誉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理事。曾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和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
今年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95周年。我们在周口店遗址获得的科学发现与研究成果并非一蹴而就,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裴文中的坚持和执着。
在裴文中身上体现出的自强不息的科学探索和创新精神,至今对学术界有深刻的影响。今年1月19日是裴文中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科学家。
1929年12月2日傍晚,日落西山,寒风呼啸。北平周口店龙骨山半山腰的洞穴里,昏暗的烛光下,一名青年用颤抖的双手,捧起刚刚从沉积物中撬出的一块看似石头的圆疙瘩。不久,位于北平西城兵马司胡同9号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收到一封电报:“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这个不起眼儿的圆疙瘩就是轰动世界的科学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化石。而这位青年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裴文中。
裴文中不仅第一个发现了北京猿人头盖骨,还发现和论证了北京猿人的石器及用火证据,开展了哺乳动物化石和地层学研究,日后又于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重要建树,并且在考古人才培养和博物馆建设等方面有重大贡献。
为生计所迫,“文青”转行到周口店
1904年1月19日,裴文中出生于河北丰南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192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年转入地质系本科。大学时代的裴文中是一位“文青”,怀着启发民智、文学救国的强烈社会责任,积极研究平民文学并组织平民文学研究会。
他在《平民文学的产生》一文中表明心志:“我们想利用平民文学的伟大势力,以改造国家,挽救社会。”战乱频仍、军阀混战的故乡原野,痛苦和凄伤中的父母与乡亲,被裴文中写入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新闻纪实的《戎马声中》中。朴实无华的文字、真挚热烈的感情,让鲁迅感同身受。鲁迅将《戎马声中》编入《中国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赞誉其为中国“乡土文学之一种”。
但文学最终没能留住这位怀揣救国救民宏愿的青年。1927年秋末冬初,裴文中为生计所迫,走进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9号,恳请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地质学家翁文灏,让他做一名实习生。
翁文灏先是安排他给一位古生物学家做临时助手。在此期间裴文中完成了一篇有关三叶虫的研究论文。那位古生物学家看后不以为然,建议所长不要录用。但翁文灏仍给裴文中发了酬金,之后安排他随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赴周口店发掘工地,做管理民工、账目等杂务工作。
不承想,裴文中在周口店开启了辉煌的学术生涯。
有志用功,跨过古脊椎动物学门槛
1928年春,裴文中来到周口店,蜗居在低矮的小客店里,每天与承担发掘工作的工人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星期,没有例假,除了大雨大雪,工作概不停止。”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中国现代地质学奠基人、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丁文江常把这句话讲给他的学生和同事听,并且立下一条规矩:“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
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裴文中用行动证明,中国学者不仅可以走出书斋,而且能够扎根田野,创造奇迹。翁文灏在为裴文中的第一部科普著作《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所作序中写道:“这册书实是中国科学研究中极重要的一本著作。因为周口店的采掘几乎是中国为物质科学之研究而做的采掘工作中最早与最大的一个。工作方法愈做愈加讲究,担任实地工作的人为数虽不甚少,但裴文中先生出力最多,占时最久。采掘的计划虽有步(达生)、德(日进)、杨(钟健)诸位先生讨论筹划,但实地组织及执行几乎全靠裴先生之力,而且有许多重要标本都由裴文中先生亲手发见。”
做到这点,实属不易。初到周口店工地之时,工人向裴文中展示随地捡得的石头,说这是“鹿牙”、那是“鸟骨”,着实让学地质而毫无古生物学基础的裴文中吃惊不小:“我真是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
学!裴文中下决心啃下这些“硬骨头”。一方面开始自学,他从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淘”到一本1925年出版的、全英文《古生物学》,把其中的“哺乳动物册”反复阅读,时时翻看,硬是把这部“洋砖头”读完了。
另一方面,裴文中当时有一个最大优势,可以常常向法国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德日进等科学大家请教。他一边读名著一边看标本消化吸收,终于跨过了古脊椎动物学这道高高的门槛。
与裴文中同在周口店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回忆,当年他们有一本宝贝图书,叫作《哺乳动物骨骼入门》。那是裴文中找来的一部英文书。他们白天干活,晚上挑灯读书,对新知如饥似渴。贾兰坡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也没到国外留过学,但是在周口店什么都能学到。”
此后,在1935年裴文中还远赴法国巴黎大学,师从国际史前学研究权威、巴黎大学教授步日耶,接受正规的史前考古训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学会了法语,还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石器与非石器之区别》。学成归来的裴文中开创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
翁文灏曾说,裴文中在周口店的成绩是他“有志用功”的结果。边学边干、刻苦钻研、勤勉敬业,便是对他“有志用功”的诠释,也是他成为卓越的科学大家和多个学科领域创始人的秘诀。
25岁,发掘出那块震惊世界的头骨
1929年注定是孤独而伟大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学院联合成立了专门发掘与研究周口店的新生代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也是在这一年,因周口店野外发掘久未见到有价值的材料,周口店野外工作负责人杨钟健和新生代研究室顾问德日进等到其他地方考察,主持周口店发掘的重担落在了年仅25岁的裴文中的肩上。
裴文中在日后这样记述当时的心境:“山中顿觉岑寂,而过起孤独的生活。那时我正因私人生活而感到烦恼,而山中工作,又遇到第五层的下部,坚硬异常,我们如何崩炸,都不见效,因之觉得山中工作颇有‘鸡肋’之感。”
至11月底,天气渐冷,经费告罄,北平方面催促他尽快停工。但因前期工作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心有不甘的裴文中决定再坚持一下。至12月,夜长日短,不得不结束的时候,采掘面上又露出一个小洞口。当时的裴文中并不知道这个日后轰动世界的“猿人洞”的深浅,好奇心与责任感驱使他腰系绳索,从山顶悬吊着下到洞中。
裴文中后来回忆说:“我觉得我既负这开掘的责任,就应当身先士卒。正如打仗一样,将官若退缩不前,最好这样仗不必打,打也必败。”下到洞底之后,他发现了很多化石,于是不顾天气寒冷,决定再继续发掘几天。
没承想,第二天,也就是12月4日下午4点多,在阴冷昏暗的洞内,借助蜡烛的微光,裴文中奇迹般地发掘出那个震惊世界的头骨化石。正是这份在荒野中的寂寞和坚持,让裴文中“唤醒”了五六十万年前人类祖先的记忆。
执着、探索、创新,得到学界认可
“幸运”地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后,裴文中没有停止脚步,他急切地要找到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遗物、遗迹,以充分证明这里是古人类生存过的地方。
在1929年的发掘中,裴文中发现了一些锋利的石英石片和颜色黑褐的动物化石。他把这些材料作为疑似的石制品和古人类使用过火的遗迹收集起来。1931年,在发掘鸽子堂的过程中,裴文中发现了更多的石英断块、碎片和疑似灰烬堆积。以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发现这处遗址时曾关注过地层中露出的锋利石英片,认为它们可能是古人类制作的工具。
此刻,裴文中陷入了思考:周口店山洞中不出产石英,这些石英碎片应该是人力搬运而来,换句话说,这是被古人类制作和使用过的石器。为此,裴文中“恶补”考古学知识,“因有此石器的发见,及研究这种石器的困难,我不能不开始学习考古学”。
当裴文中把在周口店发现的一些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英及其他岩石的石制品带回新生代研究室时,却遭到主持工作的权威们的嘲讽与批评,他们认为这些材料都是天然的石头,放到马路上都没人理会,再这样“不务正业”,就会“打饭碗”。
裴文中没有气馁和屈服。他独辟蹊径,开展实验模拟,观察自然碎石与人工制品的痕迹差异。他回忆说:“我自己耐心研究,再做试验,证明哪一块哪一个地方有人工打击的痕迹,哪一个地方是天然破碎的痕迹。我这样的研究,始终不能说服同事中的几位先生。”
面对裴文中的创新和坚持,翁文灏于1931年秋请来了步日耶作仲裁。步日耶对裴文中的研究和见解充分肯定,赞赏有加。周口店发现的石英材料确实是人类制品,一桩“公案”终于尘埃落定。
裴文中收集的疑似用火材料,经过在巴黎做化学分析和与晚期用火遗存的比对,最终被确定为古人类用火的证据。北京猿人具有用火的能力、周口店遗址保存了当时最早的人类控制用火的证据,这些内容被发文刊载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中。
经丁文江、翁文灏和章鸿钊推荐,1931年,裴文中获得了中国科学社颁发的考古学奖金。他的成就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裴文中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不断探索新的方法、新的领域。早期的周口店发掘完全采用地质古生物学的“散挖”法,在哪里发现化石就在哪里挖,现场杂乱无章。发掘者还往往避硬就软,引起化石出土层位和部位混乱。
在鸽子堂发现石器后,裴文中认识到原先方法的“草率”,数次向周口店项目负责人、加拿大学者步达生提议改革田野方法,“以免失去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或失去考古学上的重要记录”。
在得到步达生的同意后,裴文中尝试改革,却因传统习惯而受到发掘人员的抵触。“一旦改革,实属不易”,经过两天两夜的思考酝酿后,裴文中叫停了发掘工作,做新发掘方法的部署和讲解。
他将1929年参与安阳殷墟和西阴村遗址考古发掘学习到的方法加以调整和改进,采用探沟和打格画方相结合的方法,先探明“地下知识”,再确定发掘区域,画出3米×3米的方格,每一方由一个技工和一名散工负责。“开掘工作之大革命”拉开了序幕。
1933年,在发掘山顶洞时,裴文中对田野发掘和记录方法进行了更细、更深入的改革:以1米×1米为一个探方,以0.5米为一个发掘层;发掘前绘制平面图和剖面图,每天在固定位置从三个方向进行“记录照相”;对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进行系统编号,详细记录采掘时间和出产位置,等等。
为了提高效率,裴文中还设计了简单的机械,实现了运输土石和出土标本的“机械化”。他自述“开掘山顶洞的工作,是我们7年中最精密的工作、记录最详的工作、最值得注意的工作,而同时又是收获最丰富的工作”。周口店的田野发掘与记录方法,成为当时国际一流的田野操作规范,并沿用至今。
科考不止,把75岁当57岁过
新中国成立初期,裴文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为培养国家紧缺的考古专业人才殚精竭虑,四处奔走。
1952年至1955年间,裴文中发起,文化部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裴文中除担任班主任之职外,还要编写讲义、授课、指导学员田野实习。
田野考古实习是培训的重要环节,第一届培训班的全体师生兵分两路,一组去河南郑州发掘二里冈商代遗址,一组去河南洛阳发掘周汉代墓葬。发掘一段时间后,两组学员互换工地,体会遗址和墓葬的不同发掘方法。裴文中带领其中一队,并指导学员的野外实践。4期训练班共培养了346名学员,成为日后各省份文物考古事业的骨干力量,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
为解决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1956年起,裴文中和贾兰坡在周口店组织了多期古人类-旧石器考古田野培训班。田野上的裴文中,身体力行,事必躬亲。他的田野经验、田野方法和田野精神,在一期期的培训和实践中得以传承。
裴文中博学多才,为培养年轻人,言传身教,呕心沥血。他教导学生要“四勤”,即脑勤、手勤、眼勤和嘴勤,提倡“四条腿走路”,即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地质地层学的交叉协作。在带队考察期间,他不辞辛苦,见缝插针为队员授课、讲解,理论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做事例分析,传授野外求生技能和田野考古知识。
裴文中十分重视田野工作,教导学生和晚辈不要做书斋式的研究。尽管科研任务繁重、社会活动繁忙,他每年仍会抽出时间去野外做考察和发掘工作,即使在经济困难、社会动荡的上世纪60年代也不例外。他教导学生和队员说,与标本相关的一切科学信息,必须通过野外的考察和研究从实地获得,从孤立的标本上是得不到的。
裴文中野外考察时亲力亲为,不畏艰险,给后辈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57年,裴文中带队前往广西溶洞调查,寻找巨猿的原始出土地和更重要的材料。考察的重点是柳州巨猿洞,洞高约90米,地势陡峭,无路可走,需要攀着杉蒿、绳索才能进到洞里。裴文中本可坐在山脚下,等着年轻人回来汇报,他却坚持要一探究竟。就这样,年过半百的他艰难地上到山上进到洞中,并指导队员做了系统的观察与发掘。
1963年,裴文中在河套地区考察横山县雷龙湾剖面,当时可见的剖面非常陡峭并伴有流沙,即使是年轻人登上剖面顶部也相当困难。年近花甲的裴文中依旧坚持上山,哪怕是一步一滑,也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裴文中的同事、旧石器考古学专家张森水说:“为了搞清地层关系,他这个60岁的人,与我们20多或30多岁的人一样爬上爬下,观察剖面及萨拉乌苏河组与诸阶地关系,还要随时为我们讲解,其不辞辛苦的工作精神令我们非常感动。”
1948年,裴文中首先提出“河套人”的说法,对应法国学者桑志华在萨拉乌苏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代表的古人类。上世纪60年代,裴文中、张森水和汪宇平组成科学调查队,在此地区展开第四纪全面考察,将德日进和桑志华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生命不息,科考不止。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裴文中表示“要把75岁当作57岁过”,他不顾年迈体病,坚持到第一线做考古研究,到山西大同、内蒙古扎赉诺尔、贵州穿洞、河北泥河湾等地考察。
裴文中是从田野中走出的科学家。他用一生谱写了关于田野科考的乐章,华夏大地上印满了他科考的坚实足迹。1982年病逝前的一个月,他还在给家人的信中勾画自己的考察路线:9月去柳州,再去杭州,最后到安徽和县。明年去满洲里,去贵州……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曾将裴文中的科学探索历程称之为“裴文中现象”,也有学者提炼出“裴文中精神”,即家国情怀、追求真理、坚持不懈、谦虚谨慎、刚直不阿。这一“现象”和“科学家精神”,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是应该大力弘扬和传承的,是启迪和激励后人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作者:李锐洁 高星,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李锐洁 高星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