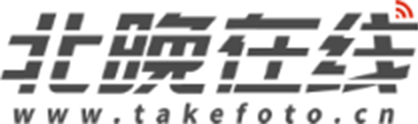2015年,入疆的第三年。那年国庆节,进入了心仪已久的尼雅。这无疑是我人生中的深重印记。

资料图
别人带着车,带着工具,我带着神圣,也没忘带一本书——里尔克的《布里格手记》。在玉龙喀什河畔未读懂,看看在沙漠深处的历史遗迹下有没有收获。
那是秋天亮丽的光线和胡杨金色叶翼飘飞的时节,我心明亮,眼界高远。
里尔克的思绪无定,他的指代连自己都糊涂。布里格眼中的医院,连自己的庭院都是。就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的沙子,绵延无尽。在和田的日子里,这本书常常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寂静和灵动,生与死,是一体两面。一本书的翻页,仿佛沙尘四起。每一页都是一个沙丘,有数不尽的沙粒。
天色完全暗下来,带入的食品和新烤制的库麦其和红柳羊肉串齐齐摆放,发出诱人的清香。小睿扬忙前忙后,兴奋异常。我在达里雅布依见过她父女俩。大家要我说句话,我说,敬尼雅!大家一阵欢呼。然后,我把里尔克的《布里格手记》拿出来,先写了尼雅之夜,然后请每人签个名,小睿扬抢着先签,稚嫩的字在火的映照下发光。
火堆,红红的火堆,枯枝随火散发出各种碎小的灰烬飞出。这时,附近干活的老乡都来了,听介绍,农大毕业回村的阿不都拉带着十来个人在此,修栈道,扎芦苇。阿不都拉略显羞涩。我请他把随行人的名字都写上。他庄严而郑重,写完后很兴奋地搓着手。
快乐的氛围在尼雅夜空延展。多年后,品味这个夜晚,生活一瞬间被点亮,燃烧。也是多年后,也就是2022年,我再次从书架上取出,我还是读不明白。我尝试进入。立冬后,天气持续晴好,我静心研读。有过沙漠困境的经历,我读着书,放任自己的心绪,甚至有几分纵容。往后所有的日子,我不恐不怖不惧,自然又自在。我如此世俗地念想和生活。
午时,窗外的阳光格外明亮。我放下了书,眼睛还在书上,看到里尔克的看。这布里格每每想什么的时候,就在看。他的看,又不是看。略一迟疑,眼光落在书端,端上一个透明的干体,书虫。我惊异于一只书虫的出现。这书虫是尼雅之夜,羊肉串的肉末残留于书端孽生的。
这书虫,把我带回尼雅之夜。沙漠深处,我们大家很快坐在一起,一个巴郎子打开手机音乐,大家围着火堆跳麦西莱普。我被阿不都拉带着,只可惜我没节奏,但还是肩脖一耸一耸地跳着。然后,一串红柳羊肉串,尽入豪肠,连里尔克、布里格都不例外。这是广袤的夜空下,一个情意深重的感召。我获得一块浸透着几千年风霜雨雪的戈壁石。《布里格手记》,成了一个我在尼雅的物证。里尔克被赋予新意,一只书虫诞生于书端,又陈尸于斯,或许世界发生巨变,经历了生与死;或许时光悠然,书虫隐于书中,不知道是否听懂了布里格没完没了的呼叫。书虫幸生于书端,看过大千世界,有着一瞬或一段时间的快乐。书虫难免一死,曾经是战战兢兢、惶恐不安的物体,甚至畏死。里尔克说,有死才有生,生活不作分别,沉重而简单。怕死就不生了,生了就要死。此生有涯,我学会并适应了顺从,随伏,和困境下的努力。
在江南的日子,谁与同坐?明月,清风,我。在清风明月拂照下,我在江河湖畔闲步,听到水流的声音,想起了尼雅河水漫漶而来。读读阿来,迟子建。阿来不说了,说说迟子建。在读过《烟火漫卷》后,我开始读《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以及五卷本散文,读出了苍凉和温暖。《布里格手记》的阴郁和《云烟过客》封面的芦苇亮丽,都在我的书桌上放光。一粒沙子的刚劲和一尾苇子的柔情,熬煮出生活的滋味。
这个时节,惊艳于一只书虫的无畏呈现。布里格说,也许,得到老了,才会靠近这一切。我想,老了,于我是好的。老了,往前走一步,就终了。这书虫,不仅老了,而且干了,附着在书端。
一只书虫,是里尔克书端上的书虫,特立,自为,羽化为仙。一本书,见证了我从江南到疆南的雄心,也目睹了我从疆南回归江南的韧性。我工作,我阅读,我回味,我抚摸从大漠带回的戈壁石,翻读着书虫栖息的书,如同抚摸和咀嚼那段岁月。于是,有了满足的叹息。即便老了,仍要不歇步,往前走。
(原标题:流绪 尼雅之夜)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丁祖荣
流程编辑:L019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版权侵权联系电话:010-85202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