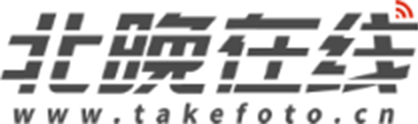编者按:前些日子,宋史研究学者张邦炜先生的两部史学旧著《两宋王朝史》和《宋代皇亲与政治》再版,并在北京召开新书座谈会,出席嘉宾包括邓小南、虞云国、包伟民、赵冬梅、李华瑞、曹家齐等多位有声望的宋史专家学者,可谓大咖云集,济济一堂。会上各位学者讨论了当前宋史研究及大众写作领域的诸多问题,尤其提到,这些年因一些自诩为“宋粉”的历史作者的碎片式、美化性书写,加之影视传媒等原因,使得现在的人们对宋朝有不少误解和非实际的想象,夸大其经济文化的片段而忽略其政治军事的全局,甚至认为宋朝是“现代社会”。这些观点都引人深思。我们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和理解这段中兴与贫弱并存的复杂历史?而历史学界面对大众又该以何种方式来书写和讲述这段历史,驱散种种“迷思”?张邦炜的两部作品或许做出了示范。


《两宋王朝史》《宋代皇亲与政治》张邦炜郑州大学出版社
随着影视作品的关注,宋史如今逐渐走入大众视野,而在史学界,宋史研究也一贯算得上“显学”,各类研究成果颇丰。
张邦炜教授在《史事尤应全面看》一文中,曾切中肯綮地谈道,宋史研究问题有四:其一是各走极端,以绝对好坏下定论,不是“积贫积弱”,便是“理想社会”;其二是片面论述,忽略整体,以局部得出结论;其三是过甚其词,过度渲染,夸大现象;其四是数据离谱。

新书座谈会上的张邦炜
就史观而言,通俗历史书写,极易将历史人物,乃至历史时段“脸谱化”“典型化”,这一做法固然出于受众考虑,但大有遮蔽史实之嫌,虚无历史之虞,使人们习惯把汉唐理解为“虽远必诛”的强盛之世,也容易把南北朝混为一谈,当作分裂动荡、无甚建树的时段……这些观点自有言说的背景,但都不能作为定论,而只能是了解与思考历史的起点。
于此角度,再读张邦炜教授两部著作,尤能见其笔意。
《两宋王朝史》作为一部王朝通史,勾勒出宋代政治的关键节点,并以突出的问题意识贯穿其间。可作为欲通识宋史者的启蒙之书,亦可作治史者提纲挈领的案头典籍。《宋代皇亲与政治》系作者专项研究,以宗室、后妃、外戚、宦官四章,讨论宋代内朝政治,可作为《两宋王朝史》的延伸阅读。
这两部著作共通的特征是史料择取精要,叙事节制恰切,结论清晰严谨。全书没有连篇累牍的引文,往往用只言片语的原文,便能很好诠释观点。此外,还恰当援引历史民谚,说明政治情势和观念。《两宋王朝史》在极有限的篇幅中,以政治史研究的理路,介绍并讨论了皇权、制度、官僚、军事等关键问题,足可见剪裁功力。更可贵的是,张邦炜教授凭借多年治史经验,敢于得出结论,且有充分判断依据,使人读之晓畅,亦有裨益。
当士大夫陷入党同伐异
建国之初,宋太祖奠定了宋代政策的基础,通过“杯酒释兵权”消除了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内部隐患。针对唐代藩镇积弊,宋朝改革军事制度,达到“强干弱枝”“重内轻外”的格局,集精兵于中央,驻重兵于都城,频繁调换节度使。
宋太祖作为军人出身的皇帝,极注重防范,他对待禁军将领往往猜忌,选用标准是“易制”;涉及边防不可不慎,其标准更多是善战,也更为信任。可见,太祖并非一味提防,而是在实际局面中,谋求动态的平衡。
待到太宗朝,雍熙北伐失败后,太宗开始重文轻武——出现将从中御、文臣统兵、宦官监军、猜忌边将的现象。张邦炜认为:“宋太宗压抑武将……使分裂动荡成为过去,内部统一安定。可是,过分压抑武将又成为宋朝积弱不武的关键原因之一。”
在文治方面,太宗延续并发展前朝政策,倡导科举、修缮典籍,其中科举影响尤为深刻,使读书蔚然成风,奠定官僚政治基础,间接瓦解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
但是,自仁宗至神宗,冗官冗兵现象日重,国家财政负担加剧,然而受制于阻力,改革始终未成,直到王安石变法,得到神宗支持,才得以彻底开展。张邦炜评价道:“熙宁变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革新运动,从总体上说具有进步意义。”它完成了“富国”的目的,表现为生产有所发展,物价趋于平稳,财政好转。接下来的“元丰改制”,“是一次成功的官制改革,但这次改革并不彻底。”而更为严重的是,元祐更化之后,政策逐渐背道而驰。
这便是北宋中后期非常显著的问题——政策缺乏连贯性,且引起剧烈党争。神宗主张改革,已有一定成效,且部分效果不佳的措施业已停止。然而,哲宗年幼,曹后主政偏于保守,启用司马光后,引起新、旧两党倾轧,张邦炜认为,“元祐年间同嘉祐时期一样,均非治世。北宋王朝的某些积弊进一步加深。”冗员更甚,财政愈难,吏治腐败。
哲宗亲政后,继承变法思路,打击元祐党人,终于使人际派别的党争,大于政策实际的争论。士大夫忙于党同伐异、勾心斗角,朝政已经难以挽救。这也直接为北宋灭亡埋下祸根。
皇帝与谁“共治天下”?
相比以出身而论的门阀政治,宋代以来大力倡导的科举,给更多精英上升空间;同时,在尊重士大夫的风气下,士大夫官僚也能更多干预政治。张邦炜在《宋代皇亲与政治》书末谈道,宋代社会被称作“官人世界”,是典型的官僚政治,士大夫确实没有杀身之虞,且受各项优待,乃至神宗有言“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但是,士大夫主导的精英政治,并不能阻止权臣“独断乾纲”。如果说北宋党争愈演愈烈,葬送万里江山;那么南宋以来的“权相”问题,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其中最著名的是秦桧,他安插亲信、培植党羽、控制言路、迫害异己,对外卑躬屈膝,迎合高宗苟且一隅的思路,在大好形势下向金国求和,最终导致“千村万落生理萧然”。
韩侂胄在“绍熙内禅”中拥立宁宗即位,由此占据政治要位。他先后打击赵汝愚,控制言路,惟用亲朋故旧,专政十四年;发动臭名昭著的“庆元党禁”,从理学中人到政治敌对,全面加以打击迫害;为巩固地位发起“开禧北伐”,也以“潦草”惨败告终。
极为吊诡的是,最终清除韩侂胄的史弥远,恰是南宋另一权臣,他的手段与韩侂胄如出一辙,擅权二十七年之久。
理宗亲政后,沉溺酒色,昏聩不堪,对内是南境各地纷乱不已,在外是蒙古大军咄咄逼人。正逢其时,贾似道走上历史舞台,他使朝政更加黑暗,推行公田法,发行新纸币,打击反对派,专政十六年,掩盖视听,以致“吏争纳赂求美职”,待到襄樊失守,竟依旧醉生梦死。
权臣专政的后果极为可怖,如果说党争是君子博弈,导致心胸狭隘;那么专权则是为一己私利,赶尽杀绝。
朱熹说“权重处便有弊”。宋代政治所呈现的问题,亦属封建皇权社会的固有问题——权力更迭极易导致政策反复,而权力集中又是天然的倾向。
笔者以为,封建皇权社会,最理想的结果,是让自身导向“制衡原则”和“精英政治”——目标应是确保精英的流动和任用,达到权力的分散和制衡。
宋代政治的“进步”,仍是局限在封建时段内部的,其核心是治理效率和效果,它源自精英参与度的提升,是影响程度的进步。而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是普罗大众权力的提升,是影响范围的进步。
宋代从未改变封建皇权政治的本质,也不能代表现代意义上的人民。名臣文彦博曾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张邦炜认为,所谓大公无私,仅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公”,代表的是官僚地主即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从内朝政治看宋朝
历史上,前后两代权力更迭时,经常爆发周期性冲突,由内朝掌权爆发危机的情势,又不在少数。
后妃、宦官、宗室、外戚所属的内朝,与士大夫所代表的外朝,矛盾由来已久,比如汉有外戚擅权、党锢之祸等冲突,晋有八王之乱、骨肉相残的斗争,唐有女皇登基、父子相争的危机……内朝往往凌驾于外朝,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而其具有的排他性,极易导致政局动荡。
张邦炜认为,在宋代权力交替中,无内朝势力,因而少内乱。宦官作为皇权分割外朝的权力工具,虽有职权,但并未凌驾于外朝之上;同时,外戚宰相如韩侂胄、贾似道等人,即便大权在握,系外朝领袖,以臣子面目出现,也谈不上内朝干政。
首先,宋代宦官干政有限,受到抑制。其实,宦官是封建皇权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是皇权的延伸,这种现象在明代最显著。一般来说,宦官势力发展,很可能与三类情况相关。其一,后妃专权,宦官成为其权势扩展;其二,刚明之主在位“刚好专任,明好偏察”;其三,昏庸之君在位,致使专权。
不难发现,宦官参与政治的契机比较广泛,这是由“人治”模式必然引起的权力再生产。然而,笔者以为最严重的问题是——宦官唯重权力,鲜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很难有士大夫的使命、约束和专业性,这就导致任人唯亲而尸位素餐,比如北宋与西夏对垒,率军惨败,更遑论废立皇帝之举。
其次,对于宗室,宋代有制度约束,足可见宋人政治智慧。概言之,对其“优之以爵禄”“不责以事权”,宗室不领兵,皇子不直接封王,不继承,位在宰相之下。同时,还有严格的结交制度,防范形成政治势力。
最后,宋代太后听政时期颇多,而没有形成乱政,实属不易。张邦炜认为,宋代太后垂帘时间比较短,像刘后、孟后都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才干,她们政治上倾向保守,且“心在社稷”,少有自立之意。
在唐代有传记的37位后妃中,牵涉政治的是25位;而宋代记载的57位后妃中,牵连者是15位。其中,最典型的是真宗朝刘后,张邦炜认为她“有武则天之心是难以求证的假设,无武则天之举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显然,内朝政治的问题,在宋代得到较好的解决。
(原标题:从“迷思”中还原宋朝 张邦炜解读两宋荣辱兴亡三百载)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赵慕宇
流程编辑:L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