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几代中国人成长的俄罗斯文学跌入低谷? 只是“剧场效应”带来错觉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今通译为薄伽丘)、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鲁迅先生晚年在给叶紫《丰收》作序中这样写道。
作者:蔡辉
插图:冯晨清
对中国文学爱好者来说,俄罗斯文学曾是最美的风景线。
自1903年第一个汉译俄罗斯文学单行本(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上海大宣书局出版)问世,至1949年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
据学者陈建华先生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计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俄苏作家多达上千位。
俄罗斯文学陪伴了几代中国读者成长,其精神诉求、审美范式、创作原则等已嵌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成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鱼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日瓦戈医生》《癌症楼》等俄罗斯小说仍是中国作家的模仿对象。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起,曾被我们视为“小说艺术巅峰”的俄罗斯文学突然“沉默”了。马尔克斯、略萨、卡佛、契佛、博尔赫斯等被反复提起,而索罗金、佩列文、乌利茨卡娅、阿库宁等成了陌生人。以阿库宁为例,他是后苏联文学时期第一位靠写小说致富的作家,可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汉译本,即《FM密码》。
俄罗斯文学究竟怎么了?真的从高峰跌入低谷了吗?其实,这一切只是“剧场效应”带给我们的错觉。
当成良药引入的俄罗斯文学
鲁迅先生曾说:“从那里面(指俄罗斯文学),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这是“五四”前贤们的共识。他们认为中俄境况相似,俄国经验更适合中国。
李大钊曾说:“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
瞿秋白则说:“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罗斯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
周作人也说:“俄罗斯文学的背景有许多与中国相似,所以他的文学发达情形与思想的内容在中国也最可以注意研究。”
从没有人追问过:中国和俄罗斯的“相似”究竟是真实的,还是错觉?
前贤追捧俄罗斯文学,实为当时日本“俄罗斯文学热”的一种转写。据学者王胜群先生研究,日本在1908年时,俄译文学种类已超英译文学,至1930年代中期,仍居翻译文学首位。
初期汉译俄罗斯小说多是留日生从日文转译而来,目的是应对时艰。
康有为曾说:“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唯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
当时国人将俄、日视为榜样,但中国留学生赴日后,发现很难融入日本社会,且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深感担忧,遂从“以日为师”转向“以俄为师”。
于是,俄罗斯文学被当成救世良药,大量引入。
俄罗斯文学为何有魅力
日本当初选择俄罗斯小说,亦有振作民族精神之意,当时日本文化界常感慨:“虽在战争中取胜(指日俄战争),却在文学上落败了。”
然而,日本学者很快反省:“日本人对于俄罗斯文学普遍感到有种土腥气,甚至觉察出西欧文学所没有的怀念与可亲。”
当时日本正从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年轻人纷纷告别土地,进入城市,可他们在情感上无法适应陌生人社会,因此对乡土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
西欧早已度过这一历史阶段,作家很少再写相关内容,所以日本读者感到“不亲切”。而俄国恰好也在此过程中,投射在创作中,赢得日本读者好感。
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认为中俄“相似”,亦属同理,但他们那是被压迫民族共同的心声,是永恒而唯一的。
此外,俄罗斯文学确实提出了许多过去中国文学未曾关注的议题。
俄罗斯文学深受东正教影响,带有强烈的弥赛亚情结,即坚信自己的价值观具普遍性,应人人奉行。与此同时,东正教认为人间充满苦难,人只有受难才能获得拯救。在东正教历史中,有“圣徒传”写作传统。圣徒们为获绝对真理,甘愿受苦,他们不断拷问自己,形成了独特的“道德神学”。
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的小说中,主人公均在忍受灵魂煎熬,并通过精神上的自我折磨,实现自我升华。
这与中国古人的“淑世精神”不谋而合,但俄罗斯文学更进一步,它精描出一个高于自我的“灵魂”。中国古代士人的信仰不甚具体、形象,只好将自己托付给历史,以“留取丹心照汗青”。而聂赫留朵夫、拉斯柯尔尼科夫、列文等人可立地实现自我拯救,他们的牺牲如此悲壮,达到熟人社会道德想象力的极致。
俄罗斯文学不只在文本上感染读者,还给出成就人格的路径与模板,它抚慰了转型中自我沦丧之痛,所以在变革社会中引起巨大共鸣。
保尔·柯察金、卓雅、舒拉、奥列格……他们曾是一代中国人的偶像。
内心深戏的贫困
深邃的主题、抒情意味的笔调、对人命运的悲悯、克制陈述的从容,拼出一个完美的文学世界,可这个世界也有巨大的短板,即:它并未回应现代性的根本之问。
现代性最终会将我们带入陌生人世界中,成为原子化的个体,被迫接受世界涂改。当我们日渐被异化时,究竟该何去何从?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文学提供的内心深戏式的解决方案显得高度不靠谱。
首先,内心深戏的元素其实是外部世界提供的,有可能蜕变成用内心将外部缺陷合法化的自欺。
其次,充满了理性主义的武断,往往用崇高来反对具体的人。
其三,主张自我应为意义而毁灭,并极力美化这一毁灭,这就背离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启蒙主题。
换言之,俄罗斯文学依然带有“厌己”的痕迹,它不断在寻找新的精神高度去跪拜,如果找不到,它便会虚拟一个。可虚拟出一个高于人性的天堂,也就虚拟出一个低于人性的地域,个体不得不在这两端摇摆。这也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性的两极——既极端包容、善良、正义和理性,同时又有酗酒、想入非非、谄媚、粗暴的一面。
周作人曾检讨自身带有两个鬼,即“流氓鬼”和“绅士鬼”,二鬼缠绕,让他痛苦万分,不得不折中:“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
可见,这一潜在的精神分裂可能是熟人社会的常态,但俄罗斯文学将其推向极致。可历经一番精神折磨后,人却并未成为现代人,社会也未达成现代性。
中国读者为何走出俄罗斯文学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曾提出一个非常有见识的观点,即:“一部诗歌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是一部重新‘绘制地图’的历史。”
以往文学史多强调传承,但布鲁姆认为,更有意义的是“误读”。正因后来作家在阅读前人文本时产生误会,并按自己的误会开始新创作,才构成了文学史。换言之,文学史就是“误读”史。他提出,拙劣的作家只会将前人奉为经典,优秀作家则与前人搏斗,只有像俄狄浦斯那样杀死“父亲”,他才能成功。
遗憾的是,俄罗斯文学太严密、太完美了,几无“误读”可能。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他的心理描写汪洋恣肆,却处处高度理性,几乎每个想法、每个动作都是现实的反应,都有深意。这就创造了一套封闭的写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评判标准变成了“准确”。
可问题在于:小说真的需要“准确”吗?何况人的心理活动本身就不够准确,在同样情境中,激活的往往是不同的反应。
“准确”的代价是无休止的细节描写,这使小说写作有了被人为割裂成“专业创作”和“业余创作”的可能。有更多文笔经验、能做到“准确”的写作者成了专业作家,而这样的专业性必以阉割创造力为代价。
托尔斯泰曾说:“写作的职业化是文学堕落的主要原因。”职业化写作必须以经典为尺度,不再直面真问题,成为“为文学而文学”,而非“为人生而文学”。
在相当时期,俄罗斯文学背离世界文学主潮,在自说自话中日渐繁琐,兼以上世纪90年代消费主义冲击,中国读者渐渐远离俄罗斯文学。
现代文学究竟好在哪
那么,该怎样回应现代性的根本之问?这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之变”。
从写实技术看,卡夫卡无法与俄罗斯文学比肩,但卡夫卡表达的是结构真实,超越了传统的细节真实。
现代人被陌生人与技术所包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一体感已经消失。对于今天读者来说,一场狂风暴雨并不意味着剧情急转直下,而只看对话,无法了解双方真实性格。现代人的生活已被拆分到无法被发生、发展、高潮、结尾概括的地步,因为每个人都扮演着更多角色,不得不多线索生存。
现代人是无根的、轻浅的,但与此同时,却拥有太多的信息浏览量,这让他们彻底放弃追寻意义的努力,因为他们明白,世界如此零碎,已无法靠意义粘合成一个整体。
面对荒诞的现实,传统小说给出的解释过于傲慢,依然强调万法归宗,试图指出唯一正确的路,而一旦沾染上这种“谜之自信”,则小说与读者之间已失沟通可能。
俄罗斯文学过于完整、过于合理,停留在用表象隐喻背后统一的简单层面,而读者喜爱卡夫卡,因为他通过一篇篇现代寓言,指出了存在的真实结构。
从卡夫卡,到加缪,到米兰·昆德拉,现代小说越来越抽离具体的历史背景,作家很少再作形象描写、景物描写,甚至不去讲一个逻辑复杂的故事,他们写的是本质的人,而非具体的人。这种写法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史,到俄罗斯文学惊觉时,已被甩开若干身位。
搞不清的“俄罗斯性”
其实,19世纪末到上世纪20年代,俄罗斯文学曾有过一个白银时代,涌现出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凡·蒲宁和帕斯捷尔纳克),此外还有别尔嘉科夫、茨维塔耶娃、别雷等,其辉煌不亚于黄金时代。
白银时代作家在文体上大胆创新,同时坚持所谓的“俄罗斯性”。
然而,究竟什么才算“俄罗斯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俄罗斯性”包含两个侧面,可用两座城市来形容:一是彼得堡,象征开放的胸襟,努力与欧洲文明保持同步;另一是莫斯科,它充满各种神话,建筑夸张、华丽,因历史上发生过4次毁灭全城的大火灾,带有“命运无常”的悲情与“凤凰涅槃”的豪迈,二者未必协调地叠加在一起。
两座不同风格的城市,象征着“俄罗斯性”的两极。
一部分白银时代作家最终转向莫斯科,将现代主义改造成一种新的抒情技巧,割裂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将文体实验变成另一种赞美工具。
另一部分白银时代作家则转向彼得堡,比如纳博科夫,他在俄罗斯写了18年小说后,在美国达到创作顶峰。然而,他的彼得堡色彩让当时其他旅欧俄罗斯作家也无法接纳他,特别是纳博科夫的心理描写都是无意义的、瞬间的,他没有回应时代的具体问题,甚至没有表现出人道主义情怀。
沃索尔金就批评说:“(纳博科夫)不仅几乎脱离了俄罗斯的现实问题,而且不受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直接影响。”
纳博科夫的遭遇展现出白银时代作家的两难:回归传统,则创作个性很可能被吞没,从而失去自我;直面创造,又会因背离“俄罗斯性”而被俄罗斯文学伟大传统开除。
在今天,人们一般认为,纳博科夫是继福克纳之后最有创造力的“美国作家”。
俄罗斯文学正在涅槃重生
错过了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了再次转型的机会,在深厚传统的支撑下,这次转型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却基本被中国读者忽略。
这批作家仍有严肃文学的情怀,但在表现上不避俚俗,更多采用现代小说手法。
以鲍里斯·阿库宁的《FM密码》为例,以侦探小说的手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进行了仿写,使普通读者也能较快速、较方便地切入原著主题。阿库宁曾是日本问题专家兼翻译,所以他的小说中常有日本元素,甚至笔名阿库宁就来自日语中的“恶人”(枭雄之意)。
索罗金的小说则以特异的叙事模式而闻名,其中不乏暴力、血腥、恐怖、污浊等内容,被不喜欢他的评论家斥为“粪土化”。调查显示,读者认为对当今俄罗斯社会危害最大的三部书中,就有索罗金的小说《蓝色脂肪》(排名第三)。在他的作品中,《碲钉国》已有汉译本,描述了一个想象的世界,人类因战争被打回中世纪,不得不靠碲钉这种麻醉品度日。此外《特辖军的一天》《暴风雪》也有汉译本。
佩列文则被认为是“后苏联时期的文学标本”,他深居简出、思想深刻,写作带有后古典主义风格,充满幽默感。他的《“百事”一代》已有中文版,他自称:“我的这本书就是一个俄罗斯版的《西游记》故事。”佩列文写道,在《西游记》中,猴子越来越像人,而在俄国,人民却在不断努力,以使自己更像猴子。此外他的《夏伯阳与虚空》也译成中文。
乌利茨卡娅则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圣母”,她一反俄罗斯文学习惯于塑造英雄母亲的虚假叙事传统,刻画了一群疯狂报复社会的女魔头,她们用人性反对母性,致力于“把男性放逐到边缘地带,要么干脆隐去,成为缺席的存在。”她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您忠实的舒里克》《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有中文版,其中《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因其反抗性和悲剧感,尤其引人瞩目。
瓦尔拉莫夫则属于“新生代作家群体”,面对俄罗斯社会巨变,对文学日渐被冷漠感到不满,自称是“正统派”,他认为:“俄罗斯文学一向信奉的价值就是我的价值。”他的《臆想之狼》已有中文版,表达了对俄罗斯人集体无意识的焦虑。他的《生:瓦尔拉莫夫中短篇小说集》也有中文版。
当代俄罗斯文学仍保持着强大的原创力,在世界文学中具有相当地位。
怎么看懂当代俄罗斯文学
因译介不足,给中国读者以俄罗斯文学在走下坡路的印象。
以布克奖为例,当年进入短名单的小说,两三年内就会有中译本,可俄罗斯布克奖获奖作品至今仍有很多无中文版。
现代世界犹如一个个剧场,各剧场将观众拉入其中后,通过技术手段,使人们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几不辨表演与真实的区别。于是,人们的时间便被剧场所掌控,身在其中,以为正经历共同的“历史时刻”,殊不知这些“历史时刻”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沉浸在美国文学的剧场中,就会为菲利普·罗斯去世而扼腕,可对于其他剧场中的人来说,其实什么都没发生,那不过是很平常的一天而已。
现代人的时间、空间、历史、记忆等精神公地都存在着被绑架的风险,只驻足于一个剧场中,自然不知道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也就无法充分吸收人类文明更多成果。
俄罗斯文学曾是一幢巨厦,不可能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它至少会留下自己的哀叹与悔恨,只是沉浸在剧场时代中,有多少人会听到这些声音?又有多少人在反省,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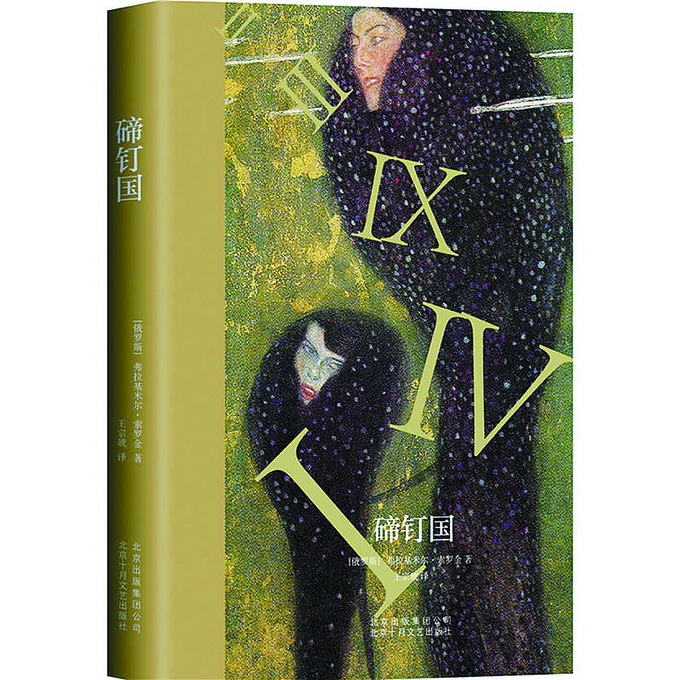
《碲钉国》 弗拉基米尔·索罗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故事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中叶的欧洲和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乌托邦、地缘政治乌托邦和技术乌托邦相继覆灭之后,欧亚大陆陷入了新中世纪。人类不再急于发展,而是试图通过“碲钉”这种高麻醉物质找到新的极乐世界,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碲钉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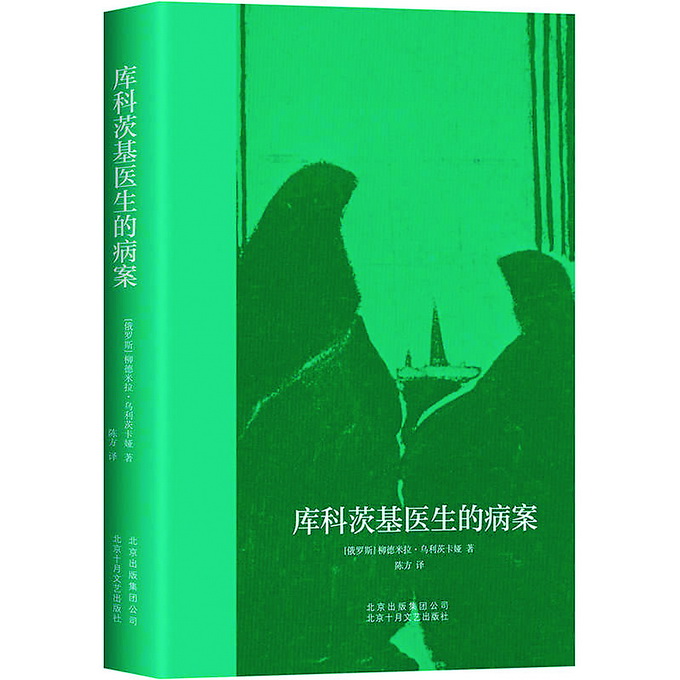
《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 乌利茨卡娅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小说围绕其中心人物,妇产科医生库科茨基,记录了两代人、两个大家庭的命运变迁。乌利茨卡娅以自己丰富的医学和生理学知识,在小说中增添了很多令人回味的细节描写,冷冰冰的科学术语在作家笔下散发出温暖而又诗意的味道。

《臆想之狼》 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小说的题目出自古老的东正教祈祷文:“愿我躲开臆想之狼。”小说聚焦1914-1918年间的俄国社会生活,作品主人公对俄国历史的选择发表意见,争论的热点有俄国人的天性、尼采主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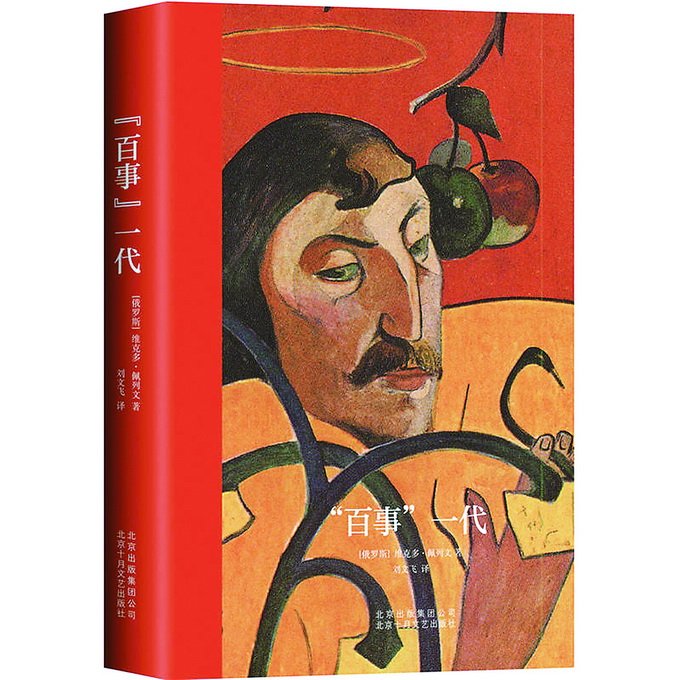
《“百事”一代》 维克多·佩列文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小说以准作家塔塔尔斯基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再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喝着百事可乐长大的一代苏联人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
(原标题: 俄罗斯文学,沉默了?)














